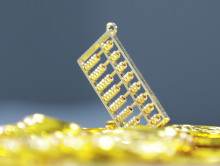中国经济学者何去何从
导读:
包括作者在内,中国的学者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取悦中国官方,内容也必须符合政治要求。对中国国内的研究机构来说,这种方式十分自然。现在,连西方学者也必须这么做了。
海外研究人员必须与中国机构合作收集资料或做研究。调查报告以官方可接受的风格进行操作,内容也必须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对中国国内的研究机构来说,这种方式十分自然,西方学者现在也必须跟着这么做。
中国的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抱怨不断,很多西方学者和中国有关系,其他人部分靠自己的力量在进行研究。
为谁研究?
我们的“自我审查”方式很多,对西方问题的关注度比中国国内还高。我们极力去解释国有企业(SOEs)的收益率,但对国有企业管理问题的揭示却望而却步,这主要来自企业面临的政治约束,或者来源于与企业有联系的所有者、雇员、供应商和购买商的政治和行政压力。在企业内部没有人敢于说话的时候,如何收集官方对国有或国营企业影响的有用信息就成为一大问题。
我们谈论着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发展的时候,仿佛这个制度环境和西方没有二致。“价格管理”规则、中央和地方都假设官员具备干预价格的超强能力。但我们接触的官方统计数据90%都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将西方“market”(市场)译为中国的“市场”,却不知道中国的“市场”一词有什么含义,仅仅是假设二者是一致的。
同样,中国的公司法里并没有提到“党”的问题,甚至党还在呼吁公司应该按公司法组建。但经过深入发掘,有些迹象还是表现得很明确的:山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都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包括公司)必须建立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还要求省属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原则上由同一人担任。从国家的角度来说,50家最大的中央企业领导由政治局指派。经济学家不会问问如果在欧美国家的企业也由党来运作会意味着什么。
作为党和政府在中央银行的部长级官员,周小川要求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指导思想“全方位推进央行的工作”。(“三个代表”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周小川形容,以“三个代表”“指导宏观经济政策”与西方的逻辑概念完全不同。但学者们在与周小川打交道时与对待西方的央行行长一样严肃认真。好像中国的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操作和影响上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太天真了吗?或者我们忽视了央行官员作为政府助手——甚至首先是党的部长这一现实?我们被假相蒙蔽了吗?或者并不愿意看到与西方经济学概念不符的现实?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我们忽视了中国有3220人是亿万富翁这一事实——而其中2932人是官员子弟。在中国最关键的5个部门——金融、外贸、国土、重大工程和证券领域,85%-90%由官员子弟控制。
每一项新的改革政策出台时,官员们都能通过这些手段使自己富裕起来:“双轨制”价格体系,不良贷款,国有企业资产剥离,投资公司和居民养老账户投资失误。混乱的、难以抗拒的农村土地向城市土地转化就是地方“领导”“系统性掠夺”的明证。地方干部投资于被要求关闭的危险小煤矿,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样获得股权的。
经济信息的缺乏“造就”了我们的研究风格。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的要求下对货币发行进行统计。这些信息很难看到。除官方统计外,各级政府部门收集和控制着国内信息,被公布的信息宣传目的很强。中国的经济学者只能从被“灭菌”的调查中寻求问题的解决途径,将模型建立在一些便利的假设基础之上:比如充分竞争、利润最大化、效益最大化、金融约束等等。[page]
还有的经济学者得到了好处。我们将政府干部与经济概念联系起来。在地方政府和党委的款待下,学者们进行着自己的研究。从他们指派的企业管理人员嘴里,我们大概是得到了所谓正确的答案。款待确实给了研究者很多好处,但他们的工作也陷入了困境。而那些介绍者不仅成为工具,甚至还成为部门斗争的牺牲品。
中国国情?
我们使用的表达方式与党的意愿一致。在党凌驾于法律和他所控制的政府前提下,“一个大多数人对法律和政府有敌意的社会”难道不适合用来描述中国?
在我们说到中国“政府”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政府里95%的“领导干部”是党员,一些关键问题必须在党委会上决定下来,政府人事部的功能实际上和党的组织部一样,而监察部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军委也是一样。是中国政府在统治着中国呢,还是这个政府只不过是贯彻党的决议的组织?在使用政府一词的时候,将中国的“政府”和西方式的政府相等同合适吗?
西方的教科书对中国的政治系统作了详细阐述,比如中国共产党的选举,党对政府和人大官员的指派,这和我们所看到的西方的政党、政府和议会是不一样的。
谁能对中国出现的卖官鬻爵的情况描述清楚?黑龙江丑闻显示了该省领导职位的价格在上涨,而任何教科书都不会对这一现象进行描述。而公众知道的价格其实和后来公布的相差多少?而买卖者似乎无所顾忌。
但不寻常的是,这重情况在中国已经被看作司空见惯了。
宣传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考。“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在中国已经被提到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地位。一个每天发生200起“群体事件”的社会难道真的稳定、和谐?
在进行信息收集和研究问题的时候,“地方政府不好,中央政府不错”这种宣传性概念被西方研究机构毫无疑问地接受下来。
我们似乎看到了“结局”:改革成功——但却并不对其中的问题提出疑问。对官方越来越多的颂歌被当做实现成功改革和解决问题这一目标的手段被忠实地执行着。没有人对靠这种政治体制能否达到目标进行怀疑。但我们对这些问题都不关心,而是选择去做那些被“灭菌”的研究和教学。
如果学术机构不这样做,那么谁愿如此?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不会,因为他们在与中国政府的交往中得到了利益。他们的银行组织需要和官方发展合作关系,合作研究必须的最后报告要经过官方的审查才能通过。西方其他投资银行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投资目的需要依靠与中国进行商业合作才能达到。
这是否说明中国研究者忽视了其工作的政治关系,以及影响其工作内容的政治因素?是否我们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时也要按照党的领导风格进行——对自我审查的问题作出勉强的回答,提供一个“清洁”的政治画卷?
以购买能力计算,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在2008到2009年将超过美国。中国是一个对西方国家纠缠日益加深的国家:四分之一的中国企业是外资所有,我们对中国提供的廉价消费品工业形成依赖。我们投资于在中国办厂的跨国公司的养老金最终对中国经济的持续提升形成依赖。但西方了解中国以及这个国家的规则吗?与西方相比,中国官方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不同理解是否会对我们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自由的选择产生影响(这恐怕已经对我们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影响)?
声明:该作品系作者结合法律法规,政府官网及互联网相关知识整合,如若内容错误请通过【投诉】功能联系删除.
相关知识推荐
据路透社报道,Google决定关闭中文搜索引擎,并将用户导向服务器基于香港的搜索网页Google.com.hk,致使600名谷歌中国员工的命运悬而未决。过去两个
核心内容: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反补贴?中国政府各部门和企业之间要积极应对反补贴调查,政府要逐步调整出口补贴政策,普及反补贴知识,完善中国反补贴立法,鼓励企业进行对外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WTO签署了双边协议,中国加入WTO曙光在前。作为朝阳产业的中国IT业,面对中国入世有什么反应?电脑厂商久炼成钢相比其
我国刑法中没有非法融资罪,非法融资行为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两种罪名都是没有死刑的。《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非法融资的行为人被判刑之后,其债务仍然应当进行偿还;被判处刑事处罚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
融资租出的固定资产属于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是指企业由于资金不足或因资金周转暂时困难或为减少投资风险,借助于租赁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而租入的固定资产。以经营
贸易融资的表现形式是进口押汇、限额内透支、进口代付、远期信用证、出口托收押汇、出口保理押汇、进口托收押汇。贸易融资是指银行对进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与进出口贸易结算
融资融券合约到期之后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对合同进行续约,但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规定,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应当
个人进行证券融资应当满足的条件包括有:年满18周岁;从事证券交易不少于6个月;开户资料规范,账户状态正常;具有收入来源和可支配财产;一定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