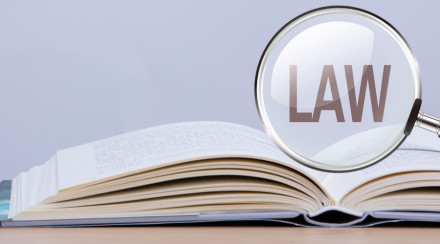刑法信条学与犯罪论体系的构筑
导读:
摘要: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可以说就是对一个个刑法信条整理、整序而成的信条学体系。刑法信条学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由于真正信条的实定法依据的尴尬,仅靠真正信条尚无法构筑犯罪论体系;不真正信条与真正信条一道构筑起刑法信条学体系;不真正信条易随着刑法学历史的变迁而变动。混入信条学的伪信条无助于体系的构筑,但引发在刑法信条学之外的刑法哲学意义上的思考。
关键词:刑法信条学;犯罪论体系;理论构筑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上,犯罪论体系乃是是一个知识的体系或者说学问的体系。那么,这一体系是关于什么的学问体系,或者说,是将什么东西加以体系化呢?我们认为,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乃是将关于刑法的一个个信条加以整理、整序而成的信条学体系。刑法信条学这个词是从德文Strafrechtsdogmatic直接翻译过来的,而信条学(Dogmatik)就是关于信条(Dogma)的理论。i 本文拟就犯罪论体系构筑前提的刑法信条学问题作一番探讨。
一、刑法信条学的概念与意义
西方国家的法学文献中,经常使用dogma、dogmatic、dogmatisch这样的用语。原本是希腊语的dogma,其最初的含义是“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被看作是正确的东西”。这个词语即使在古希腊时期也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后历经时代变迁,至17世纪以降特别成了宗教用语。也就是说,信条无论对于天主教还是对于新教,都是被“启示”出来的东西,不是仅仅凭借理性就能证明的,而是对神的权威的笃信。于是,在圣经以及天主教理解的“圣传”中,存在形形色色的信条,整理这些信条并使之体系化的学问被称作信条学。这样一来,所谓“信条神学”,就成了与圣经学和道德神学相对的一个专门的分野。
那么,从上述事实来理解近代法学,信条和信条学这样的用语可能就容易理解了。当然,法学上的信条与圣经和圣传里的信条不同,成文法里包含的“信条”,并不来自于神授,而是以承认立法者以现行法决定的事实为前提。于是,由人类制定出来的法律中有形形色色的信条,整理这些信条将之体系化的学问被称作法的信条学或者说“法信条学”。[1](P2)
所谓信条学是一个在我国法学术界较少使用的术语,常见于西方的法学著作中。依据康德的说法,法律信条论是“纯粹理性在现有理论架构上运作,而未先行批判它自身的能力”。信条论者以未经检验即视为真实的条件为前提,他在“现有的情况下”来思考。[2](P15)德国学者拉伦茨把法学直接等同于法信条学,当然,他是在狭义的法规范学的意义上作的界定。拉伦茨曾引用迈尔-科丁的论述对信条学做了解释,法信条学可以用来描述一种——以形成某些内容确定的概念,对原则作进一步填补以及指明个别或多数规范与这些基本概念及原则的关系为其主要任务的——活动。透过这种活动发现的语句,其之所以成为教条,因为它们也有法律所拥有的———在特定实证法之信条学范围内——不复可质疑的权威性。[3](P107-108)
从上面的论述出发,人们大致可以将法律中的信条理解为法律理论中不可动摇的部分。当然,信条学与法律理论这样的概念之间,也因此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区别。一般认为,相对于法学信条来说,法律理论仍然处于探讨阶段;相对于法律理论来说,信条以人们业已普遍接受为基础,是一种可以被称为一门学科基础的理论。用今天通俗的话说,信条应当是一门学科中得到广泛接受的基本理论。
那么,关于法信条学在法律理论与实践领域所承担的作用,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给出了各自的看法。德国学者罗伯特•阿列克西认为,法信条学包括以下三种活动:(1)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描述;(2)对这种法律之概念的体系的研究;(3)提出解决疑难的法律案件的建议。与之相适应,法信条学就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纬度:(1)描述——经验的纬度;(2)逻辑——分析的纬度;(3)规范——实践的纬度。[4](P311)我国学者陈兴良认为,在这三个纬度中,逻辑——分析的纬度是最重要的,因为法信条学的主要使命就在于为法的适用提供某种法律规则,因此需要对法律概念的分析,而且也包括对各种不同规范和原则之逻辑关系的考察。[5](P40)曾有德国学者在分析信条学的功能时指出,当人们将这种法官依据法律做出判决的模式,限制在判断法律文本与法律文本直接能达到的语义学内容的关系时,明显不能坚守这一模式。由于法律必然是一般地表达出来,因而连法律也不能自己解决待决的个案。尽管如此,如果应遵循法官受法律规则的约束,那也必须为法官提供法律以外的其他具体的法律规则。法律信条学的任务是准备这种规则。[6](P15)
刑法信条学是研究刑法领域中各种法律规定(die gesetzlichen Anordnungen)和各种学术观点(Lehrmeinungen)的解释,体系化和进一步发展(Fortbildung)学科。[7](P117)在德国,刑法信条学拥有一个非常完整和丰富的知识宝库,并且自李斯特和宾丁时代开始至今,也一直具有国际影响力。这特别表现在犯罪论领域。在犯罪论领域的教条主义所承担的任务中,一个重要而困难的任务就是发掘、完善和发展犯罪论的体系。所谓体系,按照康德的说法,是“各种各样的知识在一个思想下的统一”,是一个“根据各种原则组织起来的知识整体”。刑法教条主义并不满足于把各种理论原理简单地合并在一起,并且一个一个地对它们加以讨论,而是努力要把在犯罪论中产生的全部知识,有条理地放在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之中,通过这种方法,使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各个信条(Dogmen)之间的内在联系。犯罪论体系乃至整个刑法体系的内容和意义,只有通过它的完整表述,才能被完整认识。[7](P118)根据刑法信条学的主要任务,人们还可以看出,刑法信条学使用的主要是体系性的研究方法,以及问题性的研究方法。
西班牙的刑法学者金贝尔纳特•奥代格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在法律制度不太发达的国家中,信条性思考的优点可以总结如下:“在刑法信条学设定了界限和规定了概念的情况下,它就可能使刑法在安全和可预见的方式下得到运用,并能够避免非理性化、专横性和随意性。信条学越是不发达,法院的判决就越是难以预见……”。他提到了这个危险,即对法律案件的决定将变成了一种“摇奖的机会”:“信条学越不发展,摇奖的机会就越多,一直会发展到刑法混乱和无目标使用的地步……”。[7](P126)
有鉴于此,德国学者指出,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刑法教义学,其基础和界限源自于刑法法规,致力于研究法规范的概念内容和结构,将法律素材编排成一个体系,并试图寻找概念构成和系统学的新的方法。作为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桥梁的刑法信条学,在对司法实践进行批判性检验,比较和总结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解释,以便利于法院适当地逐渐翻新地适用刑法,从而达到在很大程度实现法安全和公正。[8](P53)我国学者陈兴良也指出,“刑法学如欲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推进刑法教义学方法论的研究。”[5](P40)
二、 真正信条与刑法体系
在大陆法系学者那里,成文法是信条学的“原点”。应当承认信条学这个用语本身有着非常广泛的含义,例如有时是在法律解释学的含义上被把握,这样的场合当然是以实定法为前提。另外,法学者的理论学说和判例也可能成为信条,这是广义的信条学,但不被看作是狭义的信条学。狭义的信条学的前提是以实定法包含的“信条”为对象而整理的学问。所以,教条主义者的任务不在于质疑信条,而只是对其作正确的理解,只是对其进行体系化。以这样狭义的信条作为前提的法学者坚持认为实定法是信条学的原点,也可以说是狭义法学信条学的原点和出发点。[1](P2)这些狭义的信条又可成为真正信条。
当然,如何给出这样的信条的存在理由以及根据,并非实定法学者的任务,而是法哲学者的工作。可是无论如何,只有将被清楚载明的信条学的根基发掘出来,法律学所谓的概念体系的构筑才相对容易。那么,事实上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各国刑法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司法机关适用的刑法常常具有共通性和一致性。可是,刑法理论却几乎和各国刑法学者的数量一样多。
这是因为众多优秀的刑法学者打造了自己的刑法学体系。可是,他们不是将上述狭义的刑法上的信条在实定法中加以体系化,而且也不是从这个信条演绎建造出体系,不管怎么说在刑法典中并没有载明的刑法和刑罚的目的,或者它的机能等课题。这些学者的理论活动显然是必要的和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样一来,他们的学说创建不是纯粹的信条学体系创造的方法,而具有几分哲学家的味道。总之,就广义的信条学而言,他们是某种程度上的信条主义者,例如被称作刑法学之父的费尔巴哈就是这样的学者。
可是在刑法理论世界,不同的学者对刑法目的和机能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各种体系互相对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打个比方说,各种创设的刑法体系,与其说是基于概念而构成的建造物,更毋宁说像一架组装而成的飞机。对体系这架“飞机”的内容进行整合,使之更容易在理论的天空飞翔,这是否是脱离现实世界的飞行,是值得检讨的。更进一步讲,这样的飞机,由各个不同的概念构造而成,选择哪一架飞机更能说明刑罚技术更好,这也成问题。
那么,既有的刑法体系共通的主要特征就是必先对其进行整合。若没有整合,最终理论在内容上就存在矛盾,这样的飞机无法起飞,或者会在飞行中坠毁。进一步讲,这也是刑法理论的一大特征。有人曾主张除了保留刑法信条学固有的几个信条(例如罪刑法定主义、责任主义、因果关系等),排除其他一切“信条”,理由是将不能科学证明的“信条”考虑进来,将会导致刑法体系失去整合性与科学性。[1](P4)可是,飞机不能仅凭自己的力量就飞到天上去。再说,飞机若无法正常添加燃料的话,能坚持多久也是成问题的。刑法学领域也是这样,仅凭固有的几个信条远远满足不了体系构筑的要求。
对于既有的刑法体系共同的特征,我们还是可以窥察得到的。在一定理念指导下的刑法学体系中,刑法上的既有的基本概念(行为与因果性、违法性、责任、可罚性等),都应该按照既有的体系来考察和加以说明。在体系构筑的方法上,既有传统的目的论体系的方法,又有目的理性体系机能的方法。而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如何检证这些体系的内在整合性就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1](P5)
例如,在不作为犯的场合,区分为真正不作为犯与不真正不作为犯。与此情形类似,有些刑法信条在成文法中明确记载下来,也有些刑法信条并没有在成文法中明确记载下来。前者是真正信条,后者可称作是不真正信条。真正信条一般是都得到承认的,因为它的内容不是哪个哲学家思考出来的,而是实定法客观规定出来的。
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如果将实定法规定的这些真正信条全部列举出来,并适当加以整序,那么刑法体系不就建构出来了吗?可是,这样的想法面临实际的困难。首先,虽说对真正信条加以整序是必要的,可是实定法并没有教给我们这样的顺序。若想尽量做出合理的整序,那么这个合理性并不能从实定法中直接得出。这就成了广义的信条学(不真正信条)的问题。其次,即便能够列举出这些狭义的信条(真正信条),它们的意思内容能否被正确地被理解还成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下面介绍一下一个应该受到瞩目的具有良好的整序的列举尝试。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教授弗里阿斯•卡巴伊埃劳以《法治国家犯罪理论的基本原理》为题的论文,就是效仿费尔巴哈进行了如下刑法学基本信条的整理。
(1)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actione vel sine conducta,即无行为或者举动,就无犯罪和刑罚。根据这一原理,以往的单纯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就从刑法中排除出去。
(2)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即无法律,就无犯罪与刑罚。在此,弗里阿斯•卡巴伊埃劳并没有列举费尔巴哈的名字,他指出,近代历史上贝卡利亚业已在《犯罪与刑罚》中就表述出了这个原理。
(3)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 scripta,即无成文法,就无犯罪和刑罚。根据这一原理,单纯的习惯刑法就被排除了。
(4)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 certa,即无明确的法律,就无犯罪和刑罚。刑罚法规的内容应该被明确的规定。因而,基于这个原理,犯罪类型化的要求产生出来。在内容上,与贝林所说的“无构成要件,就无犯罪”意义相同。
(5)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 praevia,即无从前的法律,就无犯罪和刑罚。这是所谓的刑法的效力不溯及原则。
(6)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 stricta,即无严格的法律,就无犯罪和刑罚。这是禁止类推解释。
(7)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iniuria,即无法益侵害,就无犯罪和刑罚。倘若立法者恪守这一的原则,就不能惩罚没有侵害法益的行为。
(8)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culpa,即无责任,就无犯罪和刑罚。此即责任主义。这一重要基本原理,同时也是争论最集中的原理。于是,卡巴伊埃劳把在阿根廷的实定法中还是仅被默认的这个原理追加上来。[1](P6-7)
那么,这样的基本原理的总结,确实具有理论魅力。可综观任何一个国家,不能说全部这些基本原理已是狭义的信条。责任主义权且不论,例如刑法上的第一信条的罪刑法定主义,就存在很多的问题。为了表述“罪刑法定主义”,费尔巴哈使用了nulla poena sine lege(无法律,就无刑罚), nulla poena sine crimine(无犯罪,就无刑罚), nullum crimen sine poena legale(无刑法,就无犯罪)这样三个简洁的命题。限于笔者所知,大陆法系的日本实定刑法上既没有这样的表述,也不能说从这些表述上立刻就能理解出它们的内容含义。思考这一信条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有必要考虑所谓“派生的原则”。可是,这种内容更细致、更具体的原则的派生,并不仅仅客观地存在于实定法中,别忘了它只是存在于刑法学者的头脑中。然后,像通常被指出的那样,这样派生的原则的形成也是基于不同的学说。
更进一步审视,有趣的问题就出来了。无论怎样强调罪刑法定主义的重要性,该原则却既没有被实定化也不存在。当前,罪刑法定主义的实定化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非常片断化的、不完整的。例如在德国,可以看到1987年的刑法典的第一条就宣告了罪刑法定主义。可是这种清楚的宣言,用弗里阿斯•卡巴伊埃劳的分类来衡量的话,也仅是nulla poena sine lege praevia(无从前的法律,就无刑罚)。[1](P8-9)
在大陆法系的日本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众所周知,日本旧刑法(1880年公布,1882年施行)第二条规定“对法律没有规定的任何行为,谁也不得处罚之”。而且明治宪法第23条规定“日本臣民,非依法律,不得受到逮捕,监禁,审问和处罚”。可是现行刑法没有有关罪刑法定主义的规定。仅仅昭和46年的改正刑法草案的第一条加入了这样的规定:“无法律的规定,对任何行为不得处罚”,这不过是改正草案的历史。可以说日本现行法包含的罪刑法定主义,是英美法系与欧洲大陆法系的结合物。
的确,日本新宪法31条规定“任何人非经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得剥夺生命和自由,也不得科处刑罚”。禁止事后法的第39条也规定:任何人对实行时适法的行为或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不得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对同一犯罪不得重复追究刑事责任。可是,这样两个规定的内容合在一起,也只是nulla poena sine lege praevia(无从前法律,就无刑罚)。总之,在实定法里,狭义的信条中占据首要地位的“罪刑法定主义”的规定确实片断地存在,但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全部实定化却也没有做到。换言之,实定法上没有的东西,要靠法学上广义的信条学补充之。于是,这一事实昭告我们两件事:一是法学的学问不可欠缺性;另一个是仅靠狭义的信条不能构筑完全的刑法信条学。
接下来,简单探讨一下刑法信条中的可以说是第二位的“责任主义”。现在,一般得到承认的基本原理是,不因为责任的存在而决定处罚,但若无责任,就不能处罚。即使实定法暗含了这样的原理,然而对于究竟什么责是任的探讨也确实是难题,也因此成了广义信条学的课题。
从逻辑的角度讲,判断某种信条是否来自实定法的规定的推理比较简单。可是,某些信条只是被实定法规定所包含,某些信条在实定法明显只是片段地规定,更有甚者连片段都不是,这三种情况就不容易区分了。
虽说罪刑法定原则部分地包含在实定法中,可是责任主义呢?
比方说,1987年的德国刑法第46条(量刑的原则)第(1)项规定:“行为人的责任(有责)是量刑的基础。”这当然是不是说责任是刑罚的基础(由于有责任所以处罚),而是说应当考虑行为者的责任。所以,假设没有责任,也就没有惩罚。进而第35条使用了“责任”这样的用语,在此被明确规定的仅仅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责任不成立。当然,这被理解为“无责任,就不处刑罚”。在日本刑法中,刑法意义上的责任的用语一度没有出现。前面提到的日本宪法第39条,规定“不追究刑事上的责任”,这也可理解为无责任就无罪。在日本刑法中,有“不处罚”紧急避难、心神丧失这样的规定,可是关于责任的理由却没有明确记载。要言之,无论狭义的信条(即真正信条)是包含在实定法中,还是可根据实定法客观上被推导出,还不能期待在实定法中将它的内容做出正确并且完全公理化的规定。[1](P10)
我们上面仅仅考察了两个真正信条——罪刑法定主义和责任主义,更遑论其他信条。别忘了各国刑法典中这样的信条差不多与刑法规定一样多,数量因国而异,属于刑法典总则的信条也有,属于刑法第二编“罪”的信条学也有。在日本的刑法典只有264条,包含的真正信条应该比较少。(可是,日本广义的信条的数量,与德国基本一样多)。
在日本,刑法典真正信条与外国相比相对较少。诸如,外国犯、含有死刑的刑种、期间计算、假释、未遂罪、并合罪、累犯、共犯、酌量减轻以及更多的各罪的类型化,等等。这些都是真正信条。但仅凭这些就力求建构“刑法体系”是办不到的。因此,须借助不真正信条的问题。[1](P11)
三、不真正信条与刑法信条学体系
大陆法系学者认为在成文法上明确记载下来的是所谓的真正信条,当然对于它们还有必要去正确揭示,可是作为狭义的信条学问题,对于以上的问题不需太过详细的追究。信条就是被一般承认的东西,因此对之的质疑本身就是矛盾的。这样的信条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根据,如何论证其正当性则不是信条学的任务。
不真正信条则具有不同的性质。它具有这样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它有着真正信条的含义,时而是从演绎,时而是从归纳中得出的,而且没有被成文法明确记载下来。因此可以说,它当然也不是刑法学者任意想象出来的东西。比方说,说2加3等于5,是运用理性回答出的,这样的不真正信条——可以认为是从真正信条中当然的推理,这并不是仅用数学的方法就能得出的东西。总之,可以说这是从真正信条及它的附加物中推理出的东西。这个附加物,即是理论的又是经验的自明之理,不加入这种附加物的考虑,任何新的信条也得不出来,只能是真正信条的反复罢了。
问题在于附加物如何在成文法中有依据呢,实际上依据的是刑法的理论家。下面对之具体说明之。一般认为,在当罚的犯罪之成立中,有必要具备“行为”、“因果关系”、“违法性”、“有责”等要件的。可是,关于这四个信条,在刑法学者之间事实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见解。所以,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作为前提的附加物是不一致的。于是,对此有无数的“学说”出现,但关于真正信条学说就没有如此的分歧。成为广义的信条学(刑法学)的课题的问题,正是这种信条。所以,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广义的信条学,不是关于真正信条的信条学,而当然成了刑法理论含义上的“刑法学”。[1](P13)
往往刑法典改正的时候,真正信条稍稍起变化,可是刑法典不改正的时候,不真正信条却也发生变化。因为,这种信条不仅是实定法而且是学问(学说)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所谓的“学派之争”(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太过闻名,人所熟知,在此不赘述。当然,成为这场学派论争焦点的,却不仅是不真正信条,对之的论争既包含不真正信条,又超越了不真正信条,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相容的刑法观之争。以下笔者要略加讨论的课题,不仅是近代的“学派之争”,而且是刑法以及刑法学整体的历史变迁所折射出的不真正信条的变动。如果用语言来描述这个漫长变迁历史的特点的,可以说就是,先是从具有外部意义的“客观主义”向具有内部意义的“主观主义”的变迁,然后是相反方向的变迁。[1](P13)我们大致可以将刑法以及刑法学的历史,划分成以下三个时代:
1、最古老的时代。当时惩罚的方法,用今天的话说,是非常客观的方法。例如,在古罗马,有所谓“形式主义”的影响,可以说完全无视内在的精神层面,毕竟肉眼可见的东西若不存在的话,法的干涉也得不到承认。这可以说仍是“客观主义”的一个表现。在罗马法上,现在已消失了的“公的犯罪”与“私的犯罪”的区别,与现在的犯罪比较起来稍显有困难,但当时犯罪的核心意义在于给他人造成侵害。
其后,尽管日耳曼法的影响渐渐增强,对人们惩罚的判断基准依然是肉眼可见的客观的结果。所谓“Die Tat totet den Mann”与“Le tait juge l'homme”这样的原则,就是这种刑法观的体现。
2、第二个时期。由于基督教与教会法的影响,考虑内心的要素的刑法渐渐朝向主观化。像学者考兰多教授指出的那样,由于1532年的卡洛丽娜刑法典导入了刑事责任,德意志刑法本该迎来新时代,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这种导入“主观的”要素的方法一天也没有用过,因而刑法新时代并没到来。
众所周知,对这个方法给予影响的是教会法。教会法重视的是“主观性”从何而来,这还只是神学意义上的“罪”的含义。应该注意的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理解“罪”及其责任的话,决不能和国家法上的“犯罪”做同样的理解。与主观地理解基督教神学上的“罪”的概念没有丝毫变迁相对,刑法上的“犯罪”概念,正如刑法史所揭示的,无法做出一个统一的定义来考察其变迁。[1](P14)
《圣经新约》中说,“所谓罪,即是违背神之法。”这个定义后来被教父和神学家更详细地加以说明。例如奥古斯汀说,“罪是违反永久法的行为或语言或希望。”这个定义揭示出,所谓罪即使没有外在的行为,也可由人们的内心完成。本文不论究神学的罪的概念,只想明确以下几点。这一定义将内心作为对神的责任来理解。于是,无论在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所谓罪经常被神眼来看待,即使人类的肉眼看不到什么结果出现,人一样仅凭内心就能完成犯罪。这样一来,这个高度“主观性”当然对教会法上的刑法而且对国家法上的刑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是将昔日客观上肉眼可见的“犯罪”变成肉眼不可见的“罪”,只是对于肉眼可见的犯罪,将肉眼不可见的东西(责任)作为犯罪成立要素考虑进来。
其后,与教会法的影响无关,刑法更准确地说刑法学向“主观化”推进了。这一主观化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刑法对作为对象的行为能更深入地、更恰当地加以解明。此外带有意识形态考虑的将刑法内心的、主观的要素完全绝对化也是原因。一个例子就是意大利的菲利普•格拉马蒂卡倡导的“主观的刑法”理论(《主观的刑法的原理》1933年)。
格拉马蒂卡认为,刑法与道德不能混同,自由意志与宿命论的问题不应该纳入刑法学中。而且,他指出刑法学在历史上是逐渐变得主观化。他主张民法上残留的客观的要素,应当从刑法上完全排除。按照他的观点,刑法上第一个主观的前提就是,行为者的责任与各种各样的主观条件。所以,违法性也被作为主观的违法性来理解。总之,在刑法上成为问题的,不是行为与结果,或者行为的危险性,而是作为主体的行为人的反社会性以及行为人的危险性。格拉马蒂卡始终一贯地持这种极端的立场。他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犯罪人被惩罚不是因为实施了犯罪这一客观事实,而是因为其实施犯罪的主观理由。因而,不仅未遂犯,就是不能未遂犯也被判断为和既遂犯一样。量刑也由责任的轻重来决定。而且,法人由于不能进行主观思考,也就没有刑事责任,不是刑法的对象。要言之,这样的见解,可以说是缓慢行进的刑法学的主观化的顶点。[1](P14-15)
3、第三个时代是二战后至今。对于全部的学问概莫能外的思想史世界所谓钟摆效应规律也存在于刑法领域。某个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摇摆到极端,今后也就自然走下坡路了。战后的刑法学也是这样,走到顶点的主观主义开始衰退了。可是,也没有完全退回到最初的位置。一言以蔽之,刑法学客观的学问方法不是将过去时代发现的主观要素驱逐出去,而只是将这种主观的要素“客观化”。当然,因为仅是理论的客观化,这样的主观要素是否改变,还是一个大问题。可是,只是思想的世界(刑法理论及其体系化)不能没有一点不可能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这种什么都客观化的倾向已到顶点,因为将责任作为“客观的责任”来理解的新尝试也出现了。[1](P16)
可是,试看一下刑法学的现状,不能断言客观主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确实,对于有关刑法的一切要素的仅仅给予客观性的验证(例如行为、构成要件、因果性、违法性)或者仅仅给予主观性的验证,这本是一时之虑。较早以前,有人主张主观的构成要件也存在,主观的违法要素也存在。关于各个具体的问题的解说,客观说也有,主观说也有。例如,大半个世纪以前德国威尔兹尔关于行为论的主张,直到今天也被认为具有精深的含义。日本的平场安治教授对之虽仍加以参考,但他同时指出“我们已不秉持行为论。这个舶来的理论存在重大的欠缺。曾先后被黑格尔主义者和宾丁认为是统一不可分割的“行为”,由于其客观的部分已经被过去毫无建树的因果关系论接纳,而其主观部分被心理责任论接纳,因而发生了断裂。”[1](P16)
总之,从刑法学的历史可以看出,不真正信条是自始至终发生着变化的。
虽然本节是以不真正信条作为课题,可是一进入刑法理论以及刑法信条学的世界,就会立刻察觉到上面理论史上问题的存在。所以,究竟不真正信条理论的领域在何处终止,刑法哲学在何处开始,明确划分出一条界线是不可能的。[1](P16-17)无论怎么说,一旦决定将刑罚和刑法整体给予这样或者那样地理解,例如作为报应刑、教育刑或者预防的理论来理解,这些理论就成了指导理念,因而会从这样的理念出发来创设出一定的刑法体系。下面,笔者力图要说明的是:仅从决定论的视点来理解和说明这些哲学的、逻辑的不真正信条。
提起“哲学的、逻辑的”,我们认为,刑法哲学与逻辑学是具有矛盾特殊性的东西。例如,因果性确实是哲学上的问题。从哲学上思考的话,“原因”与仅仅的“条件”以及“不可欠缺的条件”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内容本质上不同,应当做出区别。比方说,使房间明亮的“原因”是太阳光线,拉开窗帘只不过是房间明亮的“条件”(在夜晚即使拉开窗帘房间也不会明亮)。可是,试看刑法学者关于原因的定义,仅仅是条件的也当作原因。因此,将刑法上的原因内容用其他的——实际上异质的方法加以限定就是必要的。(例如,所谓的“相当说”就导入了这样的东西)。而且,因果关系既是自然科学的又是作为外在的事实被加以理解,那么在如何理解不作为犯的场合,确实是个难题。有的时候,即使是真正信条和不真正信条也无法解决问题,理论上用别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难题也是可能的,那就是刑法哲学的方法。
四、 混入信条学的伪信条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所谓潜在的信条或者说伪信条的问题。这是实定法上完全没有根据,也不能被看作单单是论者的学说和见解的命题。总之,不是“信条”,却又有意无意不加怀疑地被当作“信条”,这可以称作伪信条。[1](P18)这种信条,因为是论者炮制出来的,不能说是包含在整个的刑法体系中的。有大陆法系学者论述了两个最引人注目的命题其实是伪信条的情况,在此笔者略加以介绍。
首先一个伪信条是法与道德分离论在刑法领域的理论表现即刑事责任与道德责任完全无关这个命题。这一命题在法哲学领域属于聚讼纷纭的问题(所以,它不是法哲学上的信条)。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个近代以来提出的重大命题。假如刑事责任与道德责任应该做出区别的话,因而单纯的道德责任成立并不招致惩罚的话,这是说得通的。可是,刑事责任不包含道德责任,或者说两者毫无关系的话,这就说不过去了。有大陆法系学者认为,这样的思考误解了两点:其一,所谓道德完全是每个人(私人)的事情,与私生活一样应该是自由的,不受法律的拘束,这样的说法其实是误解。如果完全这样理解的话,其实无视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全部应受到刑法惩罚的行为,同时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另一个误解——内容上是同样的——认为因为立法者的禁止才有刑事责任,道德责任则不值一提。
可是,纵贯各国的实定法,连“道德”或者“道德律”这样的说法都没有,可仔细推敲起来,究竟能否说在法律上就宣告出法与道德的分离。进而,刑事判决中由于有“被告人的所作所为非常恶劣,而且也没有表示出反省……”这样的判决理由存在,行为人经常会被给予更严厉的惩罚,这不也是道德问题吗?要言之,在理论家的头脑当中容易分离的东西,在现实的世界划分起来却并不简单。[1](P19)
另一个伪信条的例子是刑事责任与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困难重重,因为从信条学的立场来看,在实定法中无论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都没有被规定出来。因此,刑法学者对此也是聚讼纷纭。将这些见解加以归纳的时候,首先不要忘记应该严格区分两个问题。即,(a)刑事责任与刑法(考虑具体判决的场合以及刑法学理论的场合)是否以自由意志作为必然前提以及(b)自由意志本身是否存在——这样两个问题。问题(a)是关于刑法体系的问题,具有逻辑的性质;问题(b)属于事实的问题,以事实的存在为课题(即自由意志是否存在)。问题(a)是刑法与刑法哲学的问题,问题(b)仅是哲学问题。
因为问题(a)是逻辑的问题,对之的见解,最终只有肯定论或者否定论这两个立场选择。与之相对,对于问题(b),在肯定论和否定论之外,还存在不可知论(即自由意志的存否在认识论上是不可知的,乃是超越人类认识能力的问题之立场)和怀疑主义(即使可知,那也不能否定也不能肯定)的见解。为方便起见,下面将不可知论与怀疑主义均用[?]表示,让我们对关于“刑事责任与自由意志”的诸见解作一归纳。
(a)自由意志是刑事责任的前提
(b)自由意志存在
(1) 肯定(a),也肯定(b)
(2) 肯定(a),否定(b)
(3) 肯定(a),(b)[?]
(4) 否定(a),肯定(b)
(5) 否定(a),也否定(b)
(6) 否定(a),(b)[?]
上述(1)(5)(6)的见解,可以在刑法学者和法哲学者中间见到很多相对应的观点,其他的见解也可能存在。一种见解的正当性若不能被证明的话,自然就存在六种可能性。那么,对此也有人可能说“我不清楚,我也没有任何立场”的话,总之是不理睬这些见解,以为那样问题也就不会产生。可是,这种态度很可能就等于承认了一个在实定法上不存在的信条。可是,如果承认这六个见解中的一个是正确的,将会怎样呢?
例如,持见解(5)者可能采用决定论的观点,完全将自由意志视作偶然,因而考虑否定刑法上不能无视的因果性。对于持这样观点的刑法理论家而言,决定论的命题不是伪信条,而成了刑法理论当然的前提乃至一个不真正信条。所以,从这个立场来看,其他五个见解就成了不真正信条或者说伪信条。相反,持见解(1)者认为惟有以自由意志为前提才能理解真正的责任,这是非决定论的立场。在这个场合,对于持如此立场的刑法理论家而言,承认自由意志并不是伪信条,而成了刑法理论当然的前提乃至一个不真正信条。[1](P20)
那么,我个人认为(1)的见解是正确的。所以对我而言,将其他的见解打造为不真正信条不过是无用的尝试。当然,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并非是刑法学的课题这样的说法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承认。因此,这仅是一个假设的信条。“任何专业领域,要是没有几个超越该专业领域并且在该专业领域内部无法证明的基本命题作为前提,那(该专业领域)也就不能成立”。[1](P20-21)如果这样想的话,上面的观点就是当然正确的。而且这样的前提,可以说也适用于全部的刑法体系的尝试。
自由意志和责任的神秘论认为不应去考虑人类的原因和动机,也不区分好的和坏的,认为在具体的案件中行动可以被任何起决定性的动机所决定。对此,从根据真正或不真正信条创设出来的刑法体系来解明这种神秘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将刑事责任与自由意志的关系的讨论束之高阁的做法也是不现实的。当然,这不过是笔者个人的见解,并不期待作为刑法信条学的问题获得一般地承认。尽管如此,我认为在本文中指出的东西是能证明的,即刑法信条学(刑法学)不仅是实定法上信条成立的学问,其方法论与自然科学的场合不同,有时无视刑法哲学也是不能成立的。正如德国学者考夫曼所说,哲学与信条学“二者皆无法取代对方”。[2](P16)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刑法信条学的本质在于,它从前提上回答了规范刑法学的体系或者犯罪论体系究竟是什么东西的体系化这一问题。像自然科学的数学是由众多的公理整序为一个科学的体系或曰科学门类一样,刑法学者也追求类似自然科学模式的体系,只是刑法的体系缺乏公理性,它是由一个个刑法信条的整序而成。不理解刑法信条学,就无法真正领会刑法的体系化问题,当然也无法深刻理解犯罪论的体系构筑问题。但是,在刑法信条学中,我们也应明确真正信条与不真正信条一道构筑了刑法信条学的体系。有时候,对于落入信条学的伪信条的争论,使我们也明确了刑法信条学的限度所在,有时也需要我们推进刑法哲学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Josē Llompart.刑法体系とその前提にされるドクマティク[A].西原春夫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M].第一卷.日本:成文堂,1998.
[2] [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5] 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J].法学研究,2005,(2).
[6] [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法律教义学在德国法文化中的意义[A].郑永流.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五)[M].郑永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7]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8]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声明:该作品系作者结合法律法规,政府官网及互联网相关知识整合,如若内容错误请通过【投诉】功能联系删除.
相关知识推荐
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罪判刑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相对负刑事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在我国,无论是否成年任何人犯罪都会有
1、犯罪预备,是指准备工具、制造条件2、犯罪未遂,是指由于犯罪份子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3、犯罪既遂,达到犯罪目的4、犯罪中止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的发生
核心内容:在对毒品犯罪分子量刑的时候,应当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应当判处的刑罚。具体如何适用就交由法律快车小编为您讲解。
摘要: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可以说就是对一个个刑法信条整理、整序而成的信条学体系。刑法信条学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由于真正信条的实定法依据的尴尬,仅靠真正信条尚无法
本人在国外,身份证到期可以委托家人代办。委托家人代办存在限制条件,各省市规定不一样,可以咨询当地公安机关。已申领过二代证及指纹信息录入的,在外期间居民身份证丢失
当事人在网络上赌博,数额较大的行为属于赌博罪,其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刑事拘留37天后无罪释放不可以要求赔偿。法律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