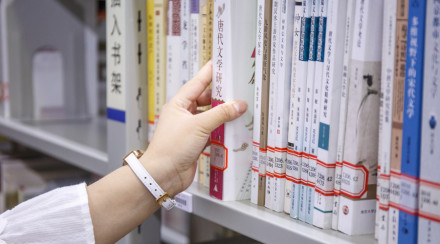我国古代刑法典探源
法律快车官方整理
更新时间:
2019-08-05
04:58:11
人浏览
摘要:加强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就古代法学海洋中的《伊训》、《周礼》、《吕刑》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以期达到某种借鉴作用。
关键词:五刑;刑法;法典
《伊训》:中国的第一部官员治罪条例
《伊训》是商朝一部重要刑事法律。成汤去位后,其孙太甲继位,辅佐他的是前朝元老伊尹。太甲年幼无知,耽于酒色,伊尹将商汤在位时已制订的《官刑》重新修订,即为《伊训》,其主要内容是:
(一)“制官刑,儆于有位”,儆即警戒;有位,即掌握一定权力。
(二)反对三种不正之风,打击十种职务犯罪。所谓“三风”,即巫风、淫风、乱风。所谓十愆,即:在宫廷内昼夜歌舞的;在官邸内酗酒的;收受贿赂的;贪恋女色的;一贯游山玩水的;一贯打猎钓鱼的;背离先王遗训、天子诏喻的;拒不接受忠言的;远离年高有德之士的;亲近娈童的。十种职务犯罪中,如“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等罪状描述具体,意思明确,“侮圣言”、“逆忠直”, 意思稍嫌空泛。据《孔传》解释,是指“狎侮圣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规而不纳”。可见对当时官吏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三)《伊训》对三风、十愆的刑事责任有所规定。所谓“家必丧”、“国必亡”,不是一般的告诫之辞,而是具体的惩罪措施。“家必丧”,即取消其在家族中的职位:“国必亡”,即剥夺其统辖封国的权力。至于“臣下不匡,其刑墨”,更为明确:臣僚和下属对犯有三风十愆的主上不加匡劝的要受到刺面之刑。
据有关史料记载,伊尹曾因太甲耽于酒色,荒于朝政,而将其放逐到桐(今山西万荣西),三年后,因太甲改悔,伊尹又将他迎回复位。据此可知,当时伊尹曾推行过一次反“三风”、“十愆”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且声势浩大,连一国之君也受到惩处。
《周礼》:中国第一部礼刑合一的综合法典
《周礼》的主要内容有:
(一)对官民的犯罪分门别类加以明确规定。《周礼·秋官·士师职》有“士之八成”的规定:“掌士之八成,一曰邦酌,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矫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根据郑玄的解释,邦酌是窃取、刺探国家机密之罪;邦贼是紊乱国政、谋反作乱之贼;邦谍是勾结外国之罪;犯邦令是抗拒君主指令之罪;矫邦令是擅自改变国家法令之罪;为邦盗是盗窃、贪污国罪;为邦朋是拉帮结派之罪;为邦诬是中伤国王、诬告臣僚之罪。老百姓也有八种主要的罪名。《周礼。地官。大司徒》规定:“以分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其中不孝、不睦均为后世所沿用。不姻即为对婚姻家庭义务的违犯;不任、不恤,是指对朋友邻里有急难、困苦时不加救助。据此可见,周代把违反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的行为纳入了犯罪的范畴,体现了礼法合一的特点。
《周礼》的另一个功能和作用,则在于积极预防犯罪。《礼纪。经解》曾阐述道:“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勤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在这些失礼、违法、犯罪行为中,最严重者莫过于犯上作乱或反叛暴乱,《周礼》正具有预防这种祸乱潮水肆意泛滥的堤防作用。[page]
(二)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刑罚体系。首先,关于五刑的确立。据《周礼》记载,周代的刑种渐成体系。《周礼。秋官》对五刑已有明确规定:“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若司寇断狱弊讼,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而以辩罚之轻重。”丘睿注云:“五刑之名,始见于虞书,然未有其目也,著其目始于此。”按此说,《周礼》是最早具体规定五刑条目的法典。
其次,关于“圜土”和“嘉石”制度的确立。我国的监狱制度,一般也认为始于周。《周礼。秋官。大司寇》称:“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罢民系对良民而言,也可以说是统治者眼中的“刁民”或“惰农”。另外,还有“嘉石”制度。“大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末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于嘉石,役诸司空。”嘉石,前人解释乃石上刻有“嘉言”,即教育人改恶从善的语录。坐诸嘉石的时间,亦有具体规定。“重垂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据郑玄的解释,这是较收聚于圜土的罪行更轻的罪过行为,即虽已有罪过,但尚未触犯刑律。这说明“圜土”、“嘉石”是对轻微犯罪的惩戒方法。
最后,关于罚金罪的确立。据《秋官·职金》载:“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它说明周代沿用了舜时“金作赎刑”的制度,而且贯彻了“罪疑惟轻”、“罪疑惟赦”的原则。
《吕刑》:第一部实体法与程序法合编的法典
据《尚书·吕刑》记载:“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即周穆王的司寇吕侯受命于穆王,本着夏朝以赎刑代替肉刑的精神,制定了《吕刑》。
(一)关于刑法的指导思想。《吕刑》继承了西周明德慎法的指导思想,主张敬德于刑,以刑教德。敬德,主要是指天子和执法官吏要有德行节操。它要求各级执法官吏,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应当具备敬德的基本品质,这就是天子敬德,如同敬天,而敬天的本质因素是保民,要既作民、臣的表率,又要使民安居乐业。因此,敬德成为明德的继续发展。《吕刑》以宽和、公允为立法的指导思想,这从“训夏赎刑”之句也可看出。《吕刑》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引述苗族无德滥刑,终遭天罚以致亡国灭嗣的教训,所谓“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吕刑》通篇强调一个“中”字。如云“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不是上天不公,而是咎由自取),“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苗族不选择优秀的司法官员,不以宽厚精神执行五刑),“罔中于信,以覆徂盟”(苗民没有评定是非的标准,只好诉诸鬼神),“民之乱,罔不中听于狱之两辞”(在百姓中引起混乱,无不在于司法官吏没有客观公正地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等。“中”的含义丰富,既有公平、正直之意,又有宽厚、适中之意。《吕刑》开篇所说“荒度作刑”,废苗族之苛法,立穆王之祥刑,也体现在“中”字上。
(二)关于定罪量刑的制度和原则。其一,量刑要结合形势。《吕刑》提出“刑罚世轻世重”,“轻重诸罚有权”。前一句讲的是宏观,即应实行“乱世用重典,盛世用轻典”的刑事政策;后一句讲的是微观,即对具体案件,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在处罚的轻重上灵活掌握,不可拘泥。“惟齐非齐,有伦有要”;齐,指统一标准;伦,是次序;要,是关键;意为办案既要依据统一的法典,又要斟酌轻重,权变处理;要分清主次,抓住关键。《尚书。蔡传》对这段解释颇为中肯:“轻重诸罚有权者,权一人之轻重也;刑罚世轻世重者,权一世之轻重也。惟齐非齐者,法之权也,有伦有要者,法之经也。”[page]
其二,将“有疑从宽”制度化。《大禹谟》虽然讲过“罪疑惟轻”,但没有具体的制度,《吕刑》继承了前代有疑从宽的精神,并且规定了具体的办法:“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非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劓、刖、宫、大辟是奴隶社会的五刑,疑赦,即有疑从宽之意。凡犯了五刑之罪,而事有可疑,不能定罪的,即改判罚金。《吕刑》规定了罚金的幅度,从百锾到千锾,视疑罪的轻重而定。此外,《吕刑》还作了“阅实其罪”的规定,即对疑罪改判罚金后,并不就此了结,还要继续查清犯罪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吕刑》的罚金是一种单独的刑种,分为五等,与五刑并立,和《舜典》所说的“金作赎刑”,以铜赎罪不同。这是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一大改革,既可保存劳动力,又可增加国库收入。《吕刑》指出“罚惩非死,人极于病”,即罚金虽不致人于死,但同样给人造成痛苦,正是对罚金刑的价值评价。
其三,实行上下比罪的比附类推制度。《吕刑》规定:“上下比罪,勿僭乱词,勿用不行。”“勿僭乱词”,即为不得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用,指援用,“勿用不行”,指不得援用无效的法律作类推、比附。
(三)关于诉讼的制度和程序。《吕刑》对诉讼中讯问、调查,证据的认定以及案卷的呈报,都有具体的规定。《吕刑》对当事人的供述极为重视。要求“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按《周礼。小司寇》之说为“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是一种察言观色的审讯方法,虽然并不可靠,但在当时,也是审判实践的总结。此外,《吕刑》还强调注意证据的准确性及供词的矛盾:“察辞于差。”必要时,应向公众调查,即到民众中去明验。注意细小的情节:“简孚有众,惟貌有稽。”西周制定的简孚制度,是明德慎刑中非常光辉的内容之一,也是对古代诉讼法中证据学的一个重要发展。
《吕刑》规定办案时,应当“惟察惟法”:一要调查案情,二要依从法律,凡是未经查实之事,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即 “无简不听”。案子在判决时,还应“明启刑书胥占”。明,是明白无误的意思;启,是打开翻阅的意思,胥为共,占为对照之意,即案件判决时,需有法官共同议定,而且应援引刑法条文。
《吕刑》对案卷材料也很重视,一案办完,必须“狱成而输”、“孚而输”,即将案卷材料如实上报。
(四)关于对司法人员的要求。重视法官选拔,明确法官责任,《吕刑》通篇充满告诫之辞:“念之哉!”“敬之哉!”可谓耳提面命,大声疾呼。同时《吕刑》非常重视司法人员的作用,把“四方司政典狱”看成是代天牧民的执政者。他们的素质如何,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三苗之所亡国绝嗣,即在于没有选择好司法官员,“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因此特别强调治国安民,所以,要选择好司法官吏,“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 何敬,非刑?”如何评价一个司法官员的内心修养和道德品质呢?《吕刑》提出了“非佞折狱,惟良折狱”,“哲人惟刑”的主张。巧言令色之徒不能担任司法职务,只有贤良明哲之士才能管好狱政。良、哲的标志可以概括为:必须敬遵天命,效忠君王:“敬遵天命,一奉我一人”;必须执法严正,操守清廉,所谓“哀敬折狱”,即对法律持敬重之心,对罪犯怀怜悯之情。对此《吕刑》有“五过之疵”的规定,列举了五种贪赃枉法的根源:“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惟官是依仗权势,袒护违法官吏;惟反是借以职权,私报恩怨;惟内是靠裙带关系走内线,在审理案件时牵制、曲解案情;惟货是敲诈勒索,行贿受贿;惟来是接受请托,贪赃枉法。周王把惩治国家官吏犯罪,看作是维护奴隶制统治的基本大政,也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对任何违法乱纪官员一概进行严肃处理,这体现了西周时期惩治职官犯罪的求实精神。五个字简明扼要,概括了以权抗法、权钱交易、人情案、关系案种种司法腐败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提出了“狱货非宝,惟府辜功”的命题,指出贪赃枉法所得的贿赂不是财富,而是罪恶的积累。这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对贪污贿赂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吕刑》对执法人员还进而提出必须勤奋工作,力诫懈怠:“罔不由慰日勤”、“罔或戒不勤”,哪怕连偶尔的一点懈怠也不容。[page]
《吕刑》成书于公元前10世纪,比罗马法早500年,比李悝的《法经》至少早800年。自两汉开始,历代《刑法志》多引《吕刑》而取法,它在中国刑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声明:该作品系作者结合法律法规,政府官网及互联网相关知识整合,如若内容错误请通过【投诉】功能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