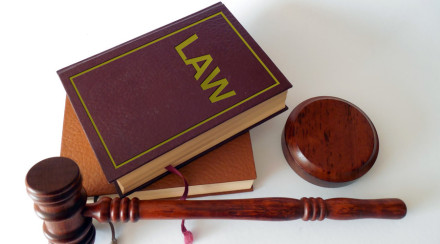【内容提要】类推解释并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令人闻之色变。其实,类推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大家在日常的司法适用中都在有意无意地采用这种分析方法来对刑法进行解释。虽说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各国在类推解释的适用上有过惨痛的教训,但这并不能说明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只要对类推解释的结构作进一步的分析,在类似性的确定上作合理妥当的限定,类推解释仍是有其发挥作用的余地的。
【关键词】类推解释 扩大解释 相似性
提到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一般都会想到禁止类推解释。因为,一般认为,类推解释实际上是允许法官立法,违反了法律只能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原则,同时,类推解释还超出了法律用语的可能含义,剥夺了公民预测自己行为后果的可能性,因此,应当禁止。⑴但是,司法实践中,明显具有类推性质的刑事司法解释为数不少,⑵同时,被禁止的类推解释和被允许的扩大解释之间的界限该如何划分,迄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因此,虽说禁止类推解释已是普遍承认的道理,但对这种道理的背景和内容,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对禁止类推解释理由的分析
所谓类推解释,通常认为,是将法无明文规定的危害行为,比照刑法分则当中最相类似的条款加以处罚,⑶即将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通过类推将其作为犯罪处理。但这是有关类推解释的最狭义理解。实际上,刑法当中,能够适用类推解释的,并不限于定罪类推,还包括量刑类推,另外,也不限定于对被告人不利的类推,还包括对被告人有利的类推。如将因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而被公安机关采取治安拘留措施的人主动如实地供述公安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犯罪行为的行为,解释为刑法第67条第2款所规定的“准自首”的场合,就是对被告人进行有利的量刑类推。因此,类推解释,说到底,也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即在需要判断的具体事实和法律规定的要件之间基本相似的时候,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
现行刑法之下,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类推解释是被禁止的。因为,通常见解认为,类推可能导致法官随意适用法律,侵害公民自由权利。⑷详言之,刑法是国民意志的体现,司法机关使用包括类推手段在内的方法随意解释法律,是对体现国民意志的刑法的侵害;同时,类推解释导致国民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后果,要么造成行为的萎缩,要么造成国民在不能预见的情况下受到刑罚处罚。⑸上述理由,概而言之,就是类推解释的缺陷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侵蚀了法律原则,二剥夺了国民预测自己行为后果的可能性。
但是,在笔者看来,上述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如果说一切犯罪和处罚都必须交由体现国民意志的立法机关通过刑法这种成文的法律加以决定,而不能交由作为国民意志的执行机关即司法机关加以决定,司法机关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通过类推的方式加以处罚,就是侵蚀了立法机关的权力,违反法律原则的话,则刑法上所有的类推解释——包括对被告人有利的类推解释——均要被禁止。但我国刑法学的通常见解都认为,对被告人有利的类推解释,在“克服形式侧面的缺陷,实现刑法正义”上具有意义,不应当被禁止。⑹同时,如果说类推解释之所以要被禁止是因为其会剥夺公民预测自己行为后果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同样是超越法律用语的通常意义而进行解释的扩大解释也会造成剥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后果,因而也应受到同样的待遇,但从众多教科书的叙述来看,学者们似乎并没有考虑过要禁止“剥夺人们预测可能性”的扩大解释。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刑事立法当中,我国现行刑法通过增设罪刑法定原则、删除1979年刑法第79条有关类推适用的条款的方式,在立法层面上确认了禁止类推的宗旨,但是,在刑法分则的条款当中,仍大量地规定了有类推适用之嫌的内容。刑法第114条就是其适例。该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条文当中,规定了5个罪名,其中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罪状都有清楚的描述,但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状则没有明确规定,而是以“以其他危险方法”这种概括性的“兜底条款”或者说“口袋条款”来加以规定的,内容含糊暧昧,其具体构成要件,只能通过学说探讨来确定。一般认为,本罪名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必须具备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必须是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以外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二是必须具有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相同或者相当的危险性。⑺其中,认定的关键是“必须具有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相同或者相当的危险性”。这种根据行为之间所具有的类似性而判断该行为也要构成犯罪的做法,实际上是典型的类推适用。但遗憾的是,在我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由于这种“兜底条款”或者‘‘口袋条款”是以法条的形式被明确规定在刑法当中的,因此,当然不会存在侵蚀成文法规定的嫌疑。但是,对具体犯罪行为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加描述,仅仅以其在某方面和法律明文规定的某种犯罪构成要件之间具有类似性为由而将该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做法,难道就没有剥夺公民预测自己行为后果结果之嫌疑吗?所以,如果说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必须禁止类推解释的话,则首先要在刑法规定当中,删除上述具有类推嫌疑的条款。
还有,刑法学的通常见解尽管排斥根据彼此之间的类似性来确定刑法适用的类推解释,但是并不反对扩大刑法用语的通常意义来进行解释的扩大解释。但殊不知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在说明原理上二者甚至可以互换。如对“隐匿”他人财物的行为是不是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的疑问,就既可以类推解释又可以扩大解释加以说明。如果说“毁坏”不限于在物理上改变其形状,而是广泛地包含使财物丧失其本来用途的一切行为的话,则使他人不能发现其财物所在,难以按照其本来用途加以利用的“隐匿”行为就当然被包括在“毁坏”的概念之内,这是扩大解释的逻辑。相反地,如果说“毁坏”被限定为在物理上改变其形状、破坏其机能的话,则仅仅让人难以发现其位置所在的“隐匿”就不能说是“毁坏”;但是,“隐匿”由于使人不能发现物之所在,难以按照其本来用途加以利用,在“难以按照其本来用途加以利用”这一点上,与在物理上改变形状、破坏机能的“毁坏”之间,具有类似之处,因此,“隐匿”财物也可以说是“毁坏”财物。这种解释方法就是类推解释。同样,在非法制造土炮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的问题上,也可以做同样的理解。如果对“枪支”做超出日常生活的理解,说其是“通过管状物体发射弹丸的武器”的话,则可以说,土炮就是枪支,这是扩大解释的逻辑。相反地,如果说尽管枪支和土炮在口径上存在差别(一般来说,枪支的口径在2厘米以下),枪支不包括土炮,但由于土炮在“通过发射弹丸,能在较远的距离上瞬间剥夺他人生命”的一点上具有类似性,所以,土炮也是枪支的话,则采用了类推解释的逻辑。如此说来,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都是一种解释方法,只是在对刑法用语进行解释时所关注的角度不同罢了。扩大解释更多地关注法律用语的可能外延,相反地,而类推解释则更多地关注法律用语所可能具有的实质内涵。
二、类推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
在刑法适用上,是否允许类推,历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虽说现在国内外的通常见解普遍认为,禁止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在学说上,怀疑其是否得以真正贯彻落实的观点,则一直不绝于耳。如德国学者萨克斯(Sax)在1953年出版的专著《论刑法上的类推适用》,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颠覆性的见解,即刑法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类推适用”原则。萨克斯的这种见解,之后为德国的另一个法学大家考夫曼(Arthur Kaufmann)所继承。考夫曼认为,除了数字之外,现实当中根本没有两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如刀跟枪之间在外观上、原理上具有非常大的差异,不过,仍然可以发现事物之间还是存在某种“存在和认识上的类似性”,而在法律适用的过程当中,将具体案件涵摄于法律规范,例如将刀、枪都涵摄于武(凶)器的概念之内,就是在进行类似性的思考,在寻找刀与枪所具有的相同点。因此,在对法律进行解释进而确定适用的过程之中,必然带有类推的成分,所谓解释与类推之间,与其说具有区别上的困难,还不如说是无法区别。所以,即便在“可能文义”的范围之内,法官所从事的法律解释与适用,仍然是在类推,“以可能文义作为界限以区分二者”的说法根本无法成立。况且,也不存在“明确而单一”的字义,字义必然有相当的模糊性,这也正意味着法律解释时类推是必然的思考工具,所以,无所谓区分禁止的类推与容许的解释可言。⑻在日本,植松正教授也认为:“法律用语,通过解释将其意义扩张,扩展到本来没有涵盖的地方,并对其加以适用的话,由于该扩张解释本来不应当扩张到似是而非的地方,所以其结局上无非是类推解释。这种现象,无非是意味着类推在某种程度上被许可。”⑼另外,伊东研佑教授也认为,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在实质上不可能被区别开来。⑽
笔者同意上述见解,认为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之间,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广义上讲,刑法适用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事实和刑法规范所规定的行为类型之间的相似性的类比或者说类推的过程。如就盗窃电力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的问题,当初,日本地方法院就持否定态度,因为,所谓财物,按照民法规定,应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体物,而电力不具有这种特性,所以,不在财物之列。但是,日本最高法院根据以下理由,撤销了这个判决。即在刑法上,适合窃取的东西就是盗窃罪的对象,不适合“窃取”的东西就不是盗窃罪的对象。所谓窃取,就是非法将他人所占有的物转移到自己的支配之下,只是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的无形的东西,由于不能被持有,所以,不能成为盗窃的对象。但是,可能持有的东西,只要是根据人的五官作用加以认识的东西就可以了,并不要求一定是有体物。因为,只要具有独立存在,能够为人力所支配的特性,就可以将其持有和加以转移。简而言之,是否盗窃罪的对象,应当根据是否能够移动以及是否可以管理来加以区别。⑾电力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能够为人所管理,能够属于盗窃罪的财物。在这里能明显地看出,之所以存在上述两个不同的判决结论,是由于法院对所谓“财物”的性质特征具有完全不同的把握。地方法院之所以说电力不是“财物”,是事先根据“有体性”来对财物进行设定,相反地,最高法院之所以说电力是“财物”,是因为其将“财物”看作为“可以管理之物”。其实,物还是一个物,只是判断者在寻找事实和刑法规范所规定的行为类型之间的相似性的角度和立场上发生了变化,因此,所得的结论也完全不同。
这样做也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司法的过程,就是将抽象的法律和具体案件进行逻辑连接,以确定该案件事实的法律效果的过程。在这个逻辑连接过程中,法律规定是大前提,具体案件事实是小前提,判决结果就是结论。而在实际的司法适用过程当中,作为大前提的法规条文尽管是静态的、固定的,但其内容,只要是在合理妥当的范围之内,就可以由法官自由加以设定的。因此,在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和法律专业知识,决定对某种行为应当加以处罚的时候,其就会在大前提的设定上,展示自己的智慧,尽量寻找和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一致的内容,从而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来。相反地,当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和专业知识,认为不应当对该事实进行处罚的时候,也会在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定的解释上,寻找和作为小前提的具体事实不一致的特征,从而得出对该事实不予处罚的结论。同样,在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已经被相对固定的场合,法官也可以对作为小前提的具体案件事实进行整理,抽象出与作为大前提对应或者不同的特征来,从而得出对该事实判断的结论。因此,司法的过程,简化为一个逻辑过程而言,实际上就是法官的目光在大、小前提之间来回移动,寻找其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得出判决结论的类比过程。
实际上,在当今的刑法学者的下意识当中,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也并非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一点从学者们就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之间的界限该如何划分,一直举棋不定的态度上,就能清楚地看得出来。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学的通常见解认为,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之间的区别取决于“法条用语可能具有的范围”。如果对某个用语所得的结论虽然超出了法条用语的本来意义,但仍在一般人所能预测的范围之内,没有让人大吃一惊,就是扩大解释;相反地,如果所得出的结论不仅超出了法条用语本来所具有的范围,而且还超出了一般人所能预测的范围,让人大吃一惊,就是类推解释。这种不考虑二者的分析过程上的差别,而仅仅从结果是否合乎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的区分标准,看起来是简明扼要、一目了然的,但是,以“一般人的预测”作为标准,应当说,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作为预测可能性主体的“一般人”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到底谁能代表一般人,也并不一定很清楚。某种解释结论是否合乎人们的预测,总不能说采取民意测验的方式对其进行检验,更不可能采用查汉语词典的方式来对其确认。因此,以“一般人的预测”这种意义不明的概念作为二者的区分标准,尽显学说在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的区分标准上之捉襟见肘。而且,从是否超出“一般人的预测”的角度来看,很多解释结论可能合情但并不合理。如尽管我国刑法只是规定“冒充军警抢劫的”要从重处罚,而没有规定真军警抢劫的该如何处理,但是,从结论上看,说“真军警抢劫的更应当从重处罚”的解释,恐怕是不会超过“一般人的预测”的。因为,在我国法律适用上,历来就有“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的传统,而且这种观念也已经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民谚所谓“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说法就是其体现。但是,从近代西方的罪刑法定观念看来,“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是典型的类推适用的体现,应当被严厉禁止。
另外,类推解释是不是一定会必然导致法官随意适用法律,具有侵害公民自由权利的危险,也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在世界发达国家当中,丹麦刑法典就规定有类推解释的规定,⑿但是,并没有人就此而指责丹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不保障人权。在德国,尽管在理论上也是反对类推解释,但在现实的刑事司法实践当中,类推适用的情形却并不鲜见。最为明显的例子,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盗窃林木的案件中,认为对使用畜力车盗窃林木的场合必须加重处罚的条款,可以适用于使用汽车盗窃林木的场合。⒀同样,在日本,尽管学术界一再表示反对,但法院也经常采用类推解释的方法来对应现实发生的案件。如公文的复印件因为和原本具有同样的社会机能和信用性,因此,被解释成是刑法第155条和第158条中所说的“公文”;⒁用电子情报处理系统制作的汽车登记档案(电子记录)被认为是刑法第157条的“公正证书的原本”,⒂这些就是公认的类推解释。
总之,类推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刑法解释方法,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我国刑法学的通说尽管在排斥类推解释,但却允许另一种与其没有多大差别的扩大解释。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并没有将禁止类推解释原则贯彻到底。
三、如何应用类推解释
实际上,包括我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的学者们都很清楚,在现实的刑事法律适用当中,类推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提倡禁止类推解释的同时,又说允许扩大解释,二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超出了法律用语所可能具有的意义,是否剥夺了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从这一点看,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在所得结论没有超越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的情形下,可能将二者无法区分开来,换言之,即便是类推解释,只要结论没有超出法律用语所可能具有的范围,剥夺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也能说是不被禁止的扩大解释。这是根据当今的刑法学的通常见解所能得出的一般推论。
既然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在分析过程上的区别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在结论上的具体妥当性,即是否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测范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该如何借助类推的方式来对刑法当中看似没有明文规定的现象进行解释,使其受到合理妥当的处理。我认为,法官心中首先必须就案件事实该如何处理有一个大致的结论,然后将目光放在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和作为小前提的具体事实之间来回移动,寻找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即相似性,最后合乎逻辑地证明自己事先所具有的结论。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关键是寻找法律规范和具体案件事实之间的类似性。这种类似性,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寻求。通常而言,说某种事实没有被刑法所明文规定,这往往是从形式上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撇开二者之间的形式上的差别,从实质上寻找和归纳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奠定对该事实适用刑法的基础。以下试举数例加以说明:
1.如枪支被抢之后没有报告,结果被他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第129条所规定的丢失枪支不报告罪?在这里,成为问题的是枪支被抢走的状态,是否属于刑法第129条所说的“丢失”。本来,“丢失”,从一般理解来看,是“遗失”,即疏忽大意或者不小心而失去的意思。枪支被抢,通常不是由于不慎或者疏忽大意而造成的,而是由于难以反抗的原因所造成的。这种情况是否属于本罪中的“丢失”呢?从“丢失”的通常意思来理解,是难以回答的。因此,只能另辟路径,从实质上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首先必须考虑枪支被抢之后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确认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然后再考虑“被抢而失去”和“遗失”之间的类似性,才能做出妥当的理解。由于枪支是一种杀伤力极大的武器,如果失去合法控制,流失到社会,必将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因此有关法律才规定,在丢失枪支之后,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以便采取有力的救济措施。因此,只要是枪支处于失控状态,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应当说是有害社会的行为。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再看“被抢而失去”和“遗失”之间的类似之处。“遗失”,一般来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不小心和失去控制,其中的关键内容是“失去控制”,而作为造成失控的原因的不小心则并不重要。换言之,“被抢而失去”和“遗失”之间,在失去控制的状态上是一致的,二者之间具有类似性,只是在失去的原因上稍有差别。从枪支被抢走之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丢失”的实质内容就是“失去控制”的角度来看,由于难以抗拒的原因而丢失枪支的场合,也可以理解为“丢失”。这种理解或许已经超出了“丢失”的通常意义,但是,得出这种结论并没有超过一般人的预测,不会让人大吃一惊。
2.通过计算机技术窃取他人密码,非法开拆、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是否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在这里,“电子邮件”是否属于刑法第252条当中所说的“信件”成为问题。我国现行刑法第252条所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其条文完全沿用了旧刑法第149条的规定,该罪的客观要件是“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这里的“信件”,在旧刑法制定的时候,其含义无疑是指“书信和递送的文件、印刷品”,其除了属于“传递信息的载体”之外,还具有“纸质”和“有形”的特征。但在当今电子信息化时代,用户之间通过电子邮箱发出或者收到的信息已经成为非常寻常的事情,这种通过互联网传递的电子邮件虽然不具有纸质和有形的特征,但同样具备传统信件所说的“传递信息载体”的特征。因此,撇开“信件”的传统意义,从“传递信息载体”这个角度来说,电子邮件和传统的书信之间应当说具有类似性。因此,电子邮件可以说属于刑法第252条所说的“信件”,窃取他人密码,非法开拆、删除他人电子邮件也是侵犯他人通信自由的行为。同样的道理,当科技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手机短信交流的时候,“手机短信”也应当属于“信件”之一种,情节严重的利用手机病毒程序、间谍程序等方式删除、破坏、非法获取他人手机中的短信的行为,必要时也可以作为侵犯通信自由罪处理。
3.组织同性恋性获利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第358条所规定的组织卖淫罪?在这里,“获利目的的同性恋”即同性之间的性交易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358条当中的“卖淫”,成为问题。本来,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卖淫”,是指“妇女出卖肉体”,⒃套用法律用语,就是“女性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男性发生性交或者实施猥亵行为”,强调的是“女性”靠“提供性服务”而“获利”。但是,在组织同性恋性获利的场合,尽管在依靠“提供性服务”而“获利”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主体上就不一定限定为“女性”了,可以是男性,而且出卖肉体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异性,既可以是异性也可以是同性。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组织同性恋性获利行为要予以处罚的话,就不能沿用原来的概念,而必须在“卖淫”和同性恋性获利现象之间确定其相似性,以将同性恋性获利现象包含到“卖淫”的概念当中去。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同性恋性获利行为和传统的“女性出卖肉体”行为一样,都是侵犯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另外,卖淫本质上是靠“提供性服务”而“获利”,只是在提供主体和提供对象上,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变化而已。早先的时候,卖淫通常是女性向男性出卖肉体,但是,后来就出现了男性向女性出卖肉体的现象,及至现在,则出现了男性向男性出卖肉体的现象,当然也会出现女性向女性出卖肉体的现象。上述现象尽管在形式上不断翻新,但是,在“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的人提供性服务”这一点上,则没有差别,这就是同性恋性获利行为和“卖淫”之间的相似性。既然如此,在刑法解释上,就可以这种相似性为根据,将“同性恋性获利的行为”理解为“卖淫”,对组织同性恋性获利的行为,按照刑法第358条所规定的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
4.变造或者倒卖变造数额较大的邮票的行为,是否可以依照刑法第227条规定的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定罪处罚?在这里,“变造”是否可以理解为“伪造”,成为问题。如从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角度来讲,伪造和变造的含义是不相同的。伪造是指按照真实的物品的外貌、形状、特征、色彩等制作物品;变造则是在真实物品的基础上采取修改、拼接、剪贴等方法进行改制,使真实物品的某一部分失去真实性,而含有假的成分。从我国刑法的数个条款均将“伪造”与“变造”分别开来加以使用的角度来看,“伪造”也显然是不能包括“变造”在内的。但是,变造以及倒卖数额较大的邮票的行为,和伪造或者倒卖伪造邮票的行为一样,都是严重扰乱国家对有价票证的管理制度的行为。而且,撇开对“伪造”的行为手段即自然意义上的理解,从其法律意义上来理解的话,应当说,所谓伪造,就是没有制作发行权的人冒用有制作发行权的他人名义,制造出外观上足以使一般人误认为是票证的行为。换句话说,在“无权制作”这一点上,伪造和变造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换言之,在“无权制作”这一点上,可以找到“变造”和“伪造”之间的相似性。因此,对变造或者倒卖变造邮票的行为按照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定罪处罚,从“无权制作”出虚假有价票证的一点上,应当说是可以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造、倒卖变造邮票行为如何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变造也包含在伪造当中,规定对于变造或者倒卖变造的邮票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7条规定的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定罪处罚。
当然,应当注意的是,在寻找法条用语和现实生活现象之间的类似性的时候,除了寻找上述所强调的二者之间的本质的一面外,还必须考虑到一般人能够接受的程度,毕竟罪刑法定原则是保护一般人的自由的原则。在从处罚的必要性的角度来看,非常合理和妥当的解释,如果完全超出了人们对用语所可能具有的理解的话,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正确的解释。如刑法第122条规定的劫持船只、汽车罪中,并不包括劫持火车的行为。虽说火车和汽车都是在陆地上行使、具有速度快、运载量大等方面具有类似性,但火车之所以为火车,就是因为其在专用的铁轨上行使,这一点是其和汽车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根据上述一些非本质的特征来描述火车与汽车之间的类似性,将汽车说成包括火车在内的解释,显然是超越了类推解释的本来意义,也超越了一般人的预测,属于不妥当的解释。
四、结语
本文无意推翻或者否定禁止类推解释原则的本来宗旨,只是想说明,类推解释并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令人闻之色变,以至于在刑事司法当中,对于很多应当处罚的现象,因为刑法没有“明文”规定而不敢大胆地进行解释,轻易地得出不能适用某条款的结论来。其实,类推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大家在日常的司法适用中都在有意无意地采用这种分析方法来对刑法进行解释。虽然从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各国在类推解释的适用上有过惨痛的教训,但这并不能说明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只要我们对类推解释的结构作进一步的分析,在类似性的确定上作合理妥当的限定,类推解释仍是有其发挥作用的余地的。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参见陈志军:《刑法司法解释应坚持反对类推解释原则》,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⑵如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通过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项规定在具备“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等三种严重情形的情况下,即使行为人不具备“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解释显然不在刑法第264条规定用语可能的范围之内。又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种解释显然也不是能够从刑法第133条的用语当中所能推导出来的。另外,具有类推之嫌的司法解释还为数不少,恕不在此一一列举。
⑶参见马克昌主编:《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⑷前注⑶,马克昌主编书,第11页。
⑸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8页。
⑹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8页。
⑺前注⑶,马克昌主编书,第358页。
⑻徐育安:《刑法上类推禁止的生与死》,
台湾元照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85-86页。另外,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9、115页、第189页以下。
⑼[日]植松正:《罪刑法定原则》,载刑法学会编:《刑法讲座第1卷》,有斐阁1963年版,第37页以下。
⑽[日]伊东研佑:《刑法解释》,载[日]阿部纯二等编:《刑法基本讲座第1卷基础理论/刑法论》,法学书院1992年版,第59页。
⑾[日]大判1902年5月21日,《刑录》第9辑第874页。另外,参见拙著:《日本刑法精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页。
⑿《丹麦刑法典》第1条前段规定“只有成文法中的可罚行为以及与此完全类似的行为,才能处罚”(Only acts punishableunder a statute or entirely comparable acts shall be punished.)。
⒀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⒁[日]最判1976年4月30日,《刑集》第30卷第3号,第453页。
⒂[日]最决1983年11月24日,《刑集》第37卷第9号,第1538页。
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13页。
【作者介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08年第5期。
黎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