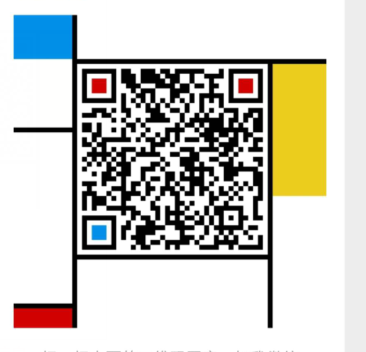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法律解释方法论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法律解释方法论
----兼以海峡两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比较为视角
蓝潮永 关今华
内容提要:法律解释学被引入认识各国不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域外典型的法国、德国、瑞士立法例进行分析;对中国是否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一直存在争议,最高院“名誉权纠纷解答”司法解释认为1987年1月的《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款是适用“公民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从法律解释方法论看,引起人们的质疑。2001年3月最高院作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对目前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规范,将“法官造法”活动推到了高潮,使中国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基本上做到了适用法律统一化,实现了较大范围的妥当性法律解释。由于中国立法机关各种立法解释的局限性,导致法官懂得运用法律解释学的力量,进行必要“造法”活动,以趋向司法统一的良好设计,谋求司法公正的伟大目标。
最高院的做法,正是“弱式妥当型法律解释方法”的体现,我国台湾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为“强式确定型的方法论”;比较研究海峡两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进行方法论,台湾的“强式确定型方法论”比大陆的“弱式的妥当型方法论”更加优越:一是适用性的范围更大;二是法律的强度更大;三是合理性证明力更大;四是确定性更大;可防止法官随意“造法”,影响法律的稳定性。因此,借鉴台湾精神损害行为法及其形成机理,不仅在运用、丰富和发展法学方法论上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在理解海峡两岸不同法律制度的立法例和司法实践,对促进海峡两岸有关法律的交流,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
自近代以来,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在侵权责任法领域里创建出一个新分支——精神损害赔偿法。目前,由于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适用的广泛性和重要性,中国是否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似乎已成定论,实际上并非如此。对我国1986年公布、1987年生效的《民法通则》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的不同理解而引发是否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由于 “赔偿损失”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包括“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从而引出了《民法通则》出台以来中国司法界和民法界各种不同的主张,直至 199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名誉权纠纷解答”)后,全国法院才统一了司法认识,认为《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款规定是适用“公民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但是这依据在法学方法论上是否可靠引起争议,之后中国又是如何发展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于是司法界和法学界又产生疑问:有的认为是法学专家故意“炒作”起来的,有的认为是法官进行“造法”活动的结果。到底如何对待中国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对此,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在总结国内外不同法律解释学时得出结论是:“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1]使用法律解释方法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具有法学方法论上的理论价值,而且可以促进各国立法和司法制度的交流和发展。
一、精神损害赔偿领域引入法律解释论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主要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以法律语言确立----------
[1]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式社
2000年版,第212页。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时,表达各自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从而法律制度引入法律解释方法的动因和理由,如众所周知的法律漏洞、法律真空、法律条文表达不明确、法条过时、法律旨意错误甚至是“恶法”等情况,其需要立法修改或解释,需要司法解释或法官造法;有的尚待法理学继续研究。对此,引起最负盛名的法学方法论的权威们的激烈争论,
导出了法律解释学产生及其运用。“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这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从此,法律解释学成为一门充满生机的学问。在此,不说外国(在国外有德奥金、哈特等),光是中国,台湾学者黄茂荣、杨仁寿、王泽鉴及大陆学者张志铭、梁慧星、张笑侠等都陆续著论法律解释学问题,各自发表了不同主张。现以法律解释方法为例,列举典型者说明之。
第一种主张,多数学者认为,法律解释的一般方法包括文义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四种。[2]第二种主张,有的学者基于分析角度不同,将法律解释方法划分为实证分析、社会分析方法和价值分析方法。[3]第三种主张,有的学者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补充、不确定法律概念和一般条款的价值补充等三类。[4]第四种主张,根据分类的标准不同,有的学者依解释的尺度不同,将法律解释方法划分为字面解释、限制解释和扩充解释。有的学者依解释的功能性,将法律解释方法划分为范围性因素、内容性因素和控制性因
-----------
[2]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6页。
[3]张笑侠:《法律解释理论体系重述》,《中外法学》1995年第1期。
[4]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200页。
素。有的学者以解释结论的确定性与妥当性强弱程度,将法律解释分为确定型解释方法和妥当型解释方法;前者是以法条文义的可能性范围为标准,凡解释结论在文义可能性范围之内的,或解释结论能反映立法者原意的,为确定型方法。后者指解释结论超出立法者原意的,或者解释结论在文义可能性范围之外的,则为妥当型方法。[5]
在本论题中,笔者趋向于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确定型和妥当型的两类法。这种分类法不足之处是,在具体运用上,除考虑法条文义之可能性范围和解释结论是否超出立法者原意之外,还必须考虑立法时的附随情况(即时代背景)和其他的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如何判断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强弱,我们提出四个标准:互相比较而言,一是适用性的范围更大;二是法律的强度更大;三是合理性证明力更大;四是确定性更大;则为“强式”方法论。反之,则为“弱式”方法论。分析域外不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解释,就是根据这些方法和标准进行学理判断的。
以域外典型的立法例观之,对《法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见第1382条)中的“损害”概念,由于立法时的时代背景,没有明文“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后出于实践的需要,被司法机关进行“扩大解释”,认为“损害”包括了“精神损害”、“人格损害”和“物质损害”等涵义,从而推导出致人损害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其适用客体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法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形成的机理是,以“扩张解释”第1382条中的不确定的“损害”概念,进行“一般条款的价值补充”,作为法国民法典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其在法学方法论上,我们称之为“强式的妥当型”法律解释方-----------------
[5]黄涌:《建立“二元化”法律解释方法适用模式的研究》,《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四期,第387页。
法论。
而《德国民法典》不同于法国法,它在“特别条款”(见第847条,第1300条)中明确提出“非财产上的损害”及赔偿概念(有的翻译为“财产损害之外的损害及赔偿” ),直接确立了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为说明方便,本文对两者不作严格区分)由于考虑当时立法时的附随情况,其适用客体受到一定的限制,法律只保护有限的几种人格利益;出于实践和人权保障的需要,司法机关采取法学方法论,将非财产损害赔偿的客体扩大适用于“一般人格权”,作为德国民法典扩大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其在法学方法论上,我们称之为“弱式的确定型”法律解释方法论。
瑞士民法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又不同于德国和法国的适用模式,其规定对侵犯“人格关系”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有两种,一种叫“损害赔偿”,是侵犯人格权所造成物质损失的赔偿,另一种叫“抚慰金”,是侵犯人格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失的赔偿,瑞士将“抚慰金”的客体扩大适用于“人格关系”,作为其民法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法学方法论上,我们称之为“强式的确定型”法律解释方法论。
其他各国和地区确立的不同精神损害赠偿制度,或是不同程度地仿效法、德、瑞士的立法,或是另辟蹊径,自成一体,但都要对如何确立该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进行法律解释,否则难以进行法律适用。由此一来,引入法律解释学认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就成为必要之大事了。
二、台湾地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解释:强式确定型方法论
台湾的精神损害行为法内容在“六法”中都有所反映,但主要集中在“台湾民法“第一编“总则”和第二编“债”之中,首先,台湾依照德国的“非财产损害赔偿”和瑞士的“抚慰金”,确立了明确的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概念,如此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法律解释方法论上属于确定型。这种确定型的方法论符合当时(20世纪30年代)中国立法背景,其法源来自内外两方面:内部法源来自清朝政府的改律变法和北洋政府修改民律活动;对外法源在于兼采德国和瑞士两国民法立法例中相关内容。由此,国民党政府跟随世界先进的潮流,从而创立了具有大陆法系特点的现代台湾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
“台湾民法”早期立法中第18条规定基本上模仿瑞士民法的第28条规定,在受害人行使人格权的损害请求权时,其法律后果采取“两分法”,分别对“损害赔偿”和“抚慰金”两项基本概念作出解释。前者中“损害”是指财产上之减损,而“抚慰金”则是专指对非财产上损害之抚慰而言,或为金钱给付,或为其他方式,例如法院判决之公布。[6]笔者对这种解释方法称之为“分别式”的文义解释。
台湾与德国法和瑞士法对人格法益保护的法律结构都由一般条款、特别条款和限制条款三个层次所构成,虽然有的内容有所差异,但基本结构是类同的。台湾法在1995年修改债法编时,增加了“身份权益”作为非财产损害赔偿的客体,体现了比瑞士法更为进步的特征,确立了以人身权为主要特征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因此,在法律解释学上,应当肯定,台湾法是在瑞士法的基础上发展了抚慰金制度,为更强式的确定型的适用模式。两种立法中的争议和区别的问题是,瑞士法中的“人格关系”是否等同于台湾法中的“人格权”?对此,瑞士学者对一般人格权或人格关系均无明确的定义。[7]唯独我国台湾学者施启扬在其对瑞
---------------
[6]Oflinger,aaO.S.40.
[7]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士民法的规定进行解释时,认为人格关系即为一般人格权。 [8]如此看来,
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格关系与人格权涵义是不同的。前者包括抽象的人格关系和具体的人格关系。抽象人格是一个建立在具体要素之上的,或者说是一个作为众多具体因素集合体的范畴。[9]而具体的人格关系虽然与主体制度有联系,主体资格是产生人格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但产生具体的人格关系还要依据具体的法律事实。因此,人格关系和人格权关系通常不仅存在着联系,人格关系涵盖了人格权关系,而且各有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大多数学者将“人格关系”等同于“一般人格权”,这违反了文义解释的旨意。所谓文义解释,按国内权威民法学专家认为,是“指按照法律条文用语之文义及通常使用方式,以阐释法律意义之内容。” [10]其是“法律解释开始,也是法律解释的终点,” [11]功用在于为法律解释活动框定一个范围内的法律合理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文义解释又可能称为范围确定型解释方法。从确定性强弱视角观之,其系以较为客观亦能
------------
[8]施启杨:《关于侵害人格权时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修正意见》,载台湾《法学丛刊》第83期,第41页。
[9]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上),《法学》第2002年第6期。
[10]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第19页。
[11]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为人们所直接或受之文义为手段,而表达出一种强式的确定性。[12]
依此看法,在法律上,作为人格关系中的人格具有多种含义,作为人的主体资格与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人格(如自由、安全等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13] 笔者赞同这种对人格关系中的“人格”的理解。人格关系中的人格与人格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格关系在处理人格与人格权之间的关系,更具有复杂性,应为上位概念,其与人格权在逻辑上具有某种交叉关系,而不是等同关系。因此,人格关系与人格权涵义是不同的。台湾法上的“人格权”,指的是瑞士法中人格关系中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如身体、健康、生命、信用、名誉等利益。这样,在法律解释方法上,对人格权的文义解释是明确的,其既包括了各种具体的法定人格利益,又包括其他非法定的人格利益和人格因素。台湾法1999年颁布的《民法债编施行法》第9条规定,不法侵害“身份法益”,应解释为,“基于父、母、子、女、配偶关系”中的各种具体的法定身份利益。因此。台湾地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机理是强式确定型方法论。
三、大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解释:弱式妥当型方法论
早期,中国大陆在处理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此类疑难案件时,由于《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如何适用的界限相当不清,从1987年至199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名誉权纠纷解答”的司法解释之前,各级法院对类同的案件是否裁判精神损害赔偿,有的认为缺乏法律依据,有的认为有法律依据。面对80年代末90年初全国掀起的二次“告记者、
------------
[12] 黄涌:《建立“二元化”法律解释方法适用模式的研究》,《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四期,第390页。
[13] 参见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报刊热”、“告作家、名人热”等高潮,最高人民法院就许多个案作出“批复”,肯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这些立法和司法当时的背景,
“迫使”最高院进行“泛立法化”举动,于
“名誉权纠纷解答”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全国法院才统一了适用“公民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认识。
最高人民法院如此做法,正是妥当型法律解释方法的体现,其合法性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和法院组织法赋予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但在法学方法论上看,立法者在形式上赋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抽象解释权力,但在客观上导致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立法的职能。因为在观念和权能上,立法者对最高人民法院的立法地位未予以认可,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从事的是一种越权的泛立法化的行为。这在法学方法论是大受质疑的。但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立法机关的先天不足所造成的各种解释局限性大量存在,导致各级法院(主要是最高院)不得不大量运用法律解释学的力量,进行大量“造法”活动,以趋向司法统一的良好设计,谋求司法公正的目标。我们应当支持。
中国大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属于妥当型的法律解释方法的理由是:该制度所依据的《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中“赔偿损失”,必须进行法律推理,其解释既在法条文义的可能范围(依传统解释,赔偿损失指赔偿经济损失或物质损失)之外,又超出立法者并无明确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原意。经过理论界的“炒作”活动,而推定“赔偿损失”包括赔偿精神损失。从侵权角度看,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或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是一种权利损害事实,该损害事实会产生另外一种后果,既可造成了财产(物质)损害的事实,又可造成了精神损害的事实(心理痛苦、精神痛苦、精神利益受到损害),不论是积极的损害事实还是消极的损害事实,权利人都可以要求赔偿财产(物质)损害和赔偿精神损害。因此,第120条中的“赔偿损失”,既可包括财产损失的赔偿,也可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从而推断出,中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推定出来的。
从妥当性角度而言,对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大抵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关于中国是否建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民法通则》第120条中“赔偿损失”是否应作为精神损失的赔偿依据,司法实践颇有争议,法律适用不统一。中国司法界和民法界出现了反对派和肯定派等各种不同的主张。反对派是以
法论》之中,详细列举了正反两派的观点和理由。[14]“肯定派”认为,公民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仅限“四权”范围(即侵害公民的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姓名权),而对法人的“三权”(名称权、荣誉权、名誉权)受侵害能否适用“精神损失赔偿”,司法实践争议很大。此阶段对精神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适用的“妥当性”处于不稳定、完全不确定之中。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地确认“公民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概念及适用因素等,否定法人存在精神损害赔偿。此阶段的司法解释是典型的“法院造法”活动,将《民法通则》第120条的两个类似条款分别适用了不同的做法,区别对待。这在法学方法论上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一是最高院如此解释法律,存在超出其权限,“泛立法化”之嫌;二是法人的人格利益受侵害,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第120条中“适用前款规定”,作出了“不统一适用法律”的逻辑解释。但可以肯定,这阶段司法解释对中国“公民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了妥当性的解释。
----------------
[14]参见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52--254页。
第四阶段,
如前文所述,根据这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确立和发展,总体上属于“弱式的妥当型方法论”。最高院在“名誉权纠纷解答”中明确地确认“公民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概念及适用因素等;在 “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中,对目前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各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些均超出立法者在《民法通则》第120条中“赔偿损失”的原意,解释结论也在文义可能性范围之外。因为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王汉斌在对《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时,也没有明确该法第120条就是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而参加制定《民法通则》的佟柔先生已经从整体上否定了120条是精神损害赔偿,而只是认为局部上,人格权受到侵害遭到的损失可以得到的“补偿”可能是精神损害赔偿,但又不是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15]可见,最高院上述如此解释法律,是一种“弱式的妥当性的方法论”。
中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确立和发展属于“推定”,其侧重于对《民
法通则》第120条的法律规定及其所涉及的“案件事实的实质内容进行
----------------
[15] 参见佟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疑难问题解答(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3页;详细内容可见关今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计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3版第13页。
价值评估或者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间进行选择的推理。” [16] 它的特点在于:“不能以一个从前提至结论的单一连锁链的思维过程和证明模式得出结论”。[17]具体适用到《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这种推定具有寻求正当性证明,要受到现行法律的约束和实践理性(被理解是当逻辑和科学不足之处人们使用的多种推理方法)检验等特点,[18]要求法官和法学家依照法律制度努力促进价值,使法律的精神与文字协调一致。[19]也就是说,应当采取辩证的思维方法,从事法律推理。因此,中国推定所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我们前文提出的判断法律解释方法论强弱的四个标准,属于弱式妥当型方法论。
四、判断不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法律解释论强弱的标准
如何判断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强弱,用于衡量不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法律解释方法的强弱程度?互相比较而言,我们提出四个标准:一是适用性的范围更大;二是法律的强度更大;三是合理性证明力更大;四是确定性更大;则为“强式”方法论;反之,则为“弱式”方法论。例如,与法国式的强式妥当型方法论不同表现在,中国推定其所适用范围是由中国最高院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多次的司法解释不断进行扩展的,法律的确定性程度较弱,法律的适用受到某些限制,不适用于“任何损害”
种类的“赔偿损失”,因此属于“弱式妥当型方法论”。不像法国的司法
---------------------
[16]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6月版,第396页。
[17]参见[英]L.乔纳森 科恩著,邱仁宗译:《理性的对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18](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区2002年版,第39页。
[19]Chain.Perelman,JUSTICE,LAW,AND ARGUMENT,D.Reidelpublishing
Company,1980,PP.128-129,135,130.
解释对一般条款(第1382条)中不确定的“损害”概念进行价值补充,扩大致“一切损害”应“负赔偿责任”,从而推导出致人损害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其适用客体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法律的确定性程度转而变强,属于“强式妥当型方法论”。
又以海峡两岸为例:我国台湾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所以为强式的方法论,其吸收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神损害赔偿制度法律解释方法论的精华,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最为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台湾法的特点是:其一,适用性的范围大。台湾抚慰金制度通过立法明定适用一般人格权,1995年又增加了适用“基于父母子女和配偶关系的身份权益”,使得台湾的抚慰金的客体不受人格权的限制,表现出很强的适用性范围。其二,其法律性的强度大。台湾确立的一般人格权和身份权益作为
抚慰金的客体,体现出强式的法律性。其三,合理性证明力大。台湾地区1929年制定民法时,基本上照搬瑞士的人格权制度。瑞士1907年制定抚慰金制度时采取广泛承认人格权的保护,由于受到德国学者的警告,改变了立法的初衷,做出了限制条款。但在1911年制定债法时,原抚慰金制度不受客体的限制,只是适用条件受到一定的限制(侵害人须存在重大过失,侵权情节重大),台湾地区“立法”时附随情况与瑞士的立法基本上类同,并且从整体上看,台湾所确立的抚慰金制度并没有受到民意和学界的反对或激烈异议,表现出较大的合理性证明力。
相对台湾法而言,我国大陆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所以是弱式方法论,理由是:首先,适用性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国《民法通则》对“四权”以推定方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尽管2001年司法解释大大扩大了该制度的适用范围,但仍受到一定的客体限制,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损害类型,因此在方法论上仍呈现出弱式的态势。其次,法律性强度较小。大陆依非一般条款即《民法通则》第120条所确立的推定式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即使后来司法解释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但仍摆脱不掉列举主义的适用模式,所以法律性的强度仍然偏小。最后,合理性证明力较小。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发现《民法通则》第120条的缺陷,实践中法官大胆造法,与时俱进,大大拓展了适用范围,但该制度的合理性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扩大适应范围中,其客体的性质仅限于人格权和人格利益,是否包括其他权益(如身份利益、财产利益),仍有争议。因此,正如“钢铁是千锤百炼炼成的”一样,中国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是经过不断法律认识,不断学理争论,不断司法实践,不断“造法”活动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比较研究海峡两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法律解释方法论,台湾的“强式确定型方法论”比大陆的“弱式的妥当型方法论”更加优越:一是适用性的范围更大;二是法律的强度更大;三是合理性证明力更大;四是确定性更大;可防止法官随意“造法”,影响法律的稳定性。因此,讨论、研究和借鉴台湾精神损害行为法及其形成机理,不仅在运用、丰富和发展法学方法论上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在理解海峡两岸不同法律制度的立法例和司法实践,对促进海峡两岸有关法律的交流,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
结论
从法律解释方法论看,中国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从1987年《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