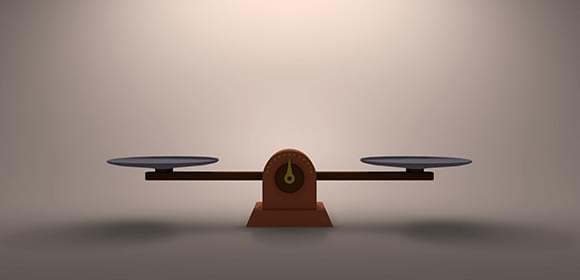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下)
导读:
五、威慑何以无效:没有代价的伪证
法官不信任证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伪证普遍,谎言盛行。调查发现,近六成法官发现过证人作伪证,其中D、E、G法院分别为96.43%、78.95%和83.33%;18.18%的法官声称未发现证人作伪证(只是未发现而已)。证言采信率低也表明在法官眼中证人的虚假陈述普遍。伪证之所以普遍,主要原因是伪证行为几乎没有代价,法律对伪证的制裁属于不可置信的惩罚承诺,威慑力不足。其中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证人证言对于证人和法官双方皆约束软化,既不能约束证人如实陈述事实,也不能约束法官对证言作出非真即假的认定——要么真实,法庭予以采信;要么虚假,证人承担伪证责任(假定证言与案件相关)。这种约束机制的双向软化相互影响,引致一个低效率的恶性循环:证人因无需承担伪证责任而普遍虚假陈述;法官因伪证盛行和顾忌证人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而对证言根本不予考虑;证言因未实质性进入司法过程(只是形式上成为案卷中的证据)为法官考虑、认定和采信,又导致证人即使虚假陈述也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法官往往不太介意,权当是证人在法庭的一场表演。
第二,从立法来看,民事诉讼中伪证的法律责任过于宽松。对作伪证的个人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对法人可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拘留期限15日以下。尽管《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了刑事责任,但《刑法》第305条将伪证罪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刑事诉讼中,而令民事诉讼中伪证罪的追究被悬空。伪证的刑事责任缺位,加上拘留措施适用较少,明显导致对伪证行为的威慑不足。
第三,从执法来看,对民事诉讼中伪证行为处罚不力,执法不严。法官未严格追究伪证行为其实内含着一种经济逻辑。惩罚是有成本的,追究伪证行为需调查取证,耗费金钱、时间和精力,可能导致诉讼拖延;而收益只是抽象的司法权威以及长远而言的法治秩序,就眼前来看,即使罚款,法官通常也无直接收益。尽管直接收益并不构成司法人员追究违法行为的必要条件,但经济分析至少可部分地说明问题。而且,证明伪证行为成立的难度较大,因为它以证人的故意为主观要件,证人陈述真假的判断是一个难以明确的标准,证人完全可诉诸各种理由——证言的可信性取决于证人的感知力、记忆力、表达力、“前见”等许多因素——而轻易脱“险”,要证明伪证罪的成立还需满足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种种困难导致民事诉讼中对伪证罪的追诉事实上几乎不可能。
真实陈述没有奖赏,虚假陈述亦无责任。调查表明,对证人作伪证的处理,多数法官(49.73%)只是批评教育,其中D法院78.57%;采取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法官14.97%(大多罚款,拘留措施的使用极少),其中H法院为0;不了了之的比例6.42%。显然,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基本上不会因作伪证而付出多大代价:批评教育和不了了之占84.99%;因伪证而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几近于零,所有被调查法院皆未出现此类案例。这样,我们就可将证人作伪证视为证人权衡各种因素——比如,作伪证帮助一方当事人会产生现实或潜在的收益,被惩罚的概率极低,惩罚承诺不可置信——后所作出的理性选择,是证人与法官博弈的结果。正如上述法官与证人的博弈分析所提示的,法官选择不信任是其最优战略。既然法律可视为一种激励机制,伪证普遍(及证人不出庭)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就可看成是现行制度所激励的结果。
证人与法官合作的实现取决于一系列规则的激励,包括奖惩规则。其中惩罚比奖赏更深刻,是合作的关键。证言为法官采信的前提是陈述真实(尽管伪证有时也可能被采信),但是证人的真实陈述不能建立在奖赏的基础上,而只能以有效威慑为条件。有效的威慑机制的关键,一是对伪证施加更严厉的惩罚,提高罚款金额,追究刑事责任,特别可考虑借鉴英美法的做法规定藐视法庭罪;二是严格执法,提高发现和惩罚伪证行为的概率。证人作伪证的预期成本不仅与惩罚的严厉度相关,更与能否有效执行有关。惩罚要令人置信,须适时适当进行检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态度——多大程度上愿意“叫真”,而这又受制于成本收益的对比。尽管法官追究伪证行为的经济激励不足,但只要对成本较小(伪证行为明显)、收益较大(行为情节恶劣)的情形坚决予以追究,也可一定程度上实现杀一儆百的威慑效应。假如被发现和惩罚的概率达20%,伪证行为将会大大减少。在刑事诉讼中,人们会有这种感受:尽管存在证人不愿作证、不愿出庭和作伪证的现象,但相比民事诉讼,证人所发挥的作用相对更大,法官对证人的信任度也更高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的收集更多涉及“威慑力往往强于法院”的公安和检察机关,刑事案件相对更“事关重大”,对伪证的制裁力度更大,发现和惩罚伪证行为的概率相对更高,因而法院的惩罚承诺更可置信。
六、谁之证人、何种出庭方式:证人与诉讼结构
“谁之证人”的问题涉及到整个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大陆法系强调证人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证人被视为“国家/法院的证人”,证人作证是对国家的义务,是否传唤证人由法官决定,证人作证的费用由法院依法定项目和金额向证人支付(尽管最终由当事人承担)。故大陆法的司法伦理不提倡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律师与证人的接触,试图通过切断这种接触而确保证言的客观性;这种接触可能成为对方攻击的理由,并往往会导致证言价值的下降。而在普通法国家,证人是“当事人的证人”,是当事人重要的诉讼武器,依附性强(尽管法律也规定证人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证人由当事人寻找和提出,证人是否出庭由当事人保障,法院通常没有确保证人出庭之义务,证人的报酬一般由当事人依法律规定支付。案件真实的发现和裁判结果的正当化,通过对抗制本身自我负责的程序保障机理,利用当事人双方竞争性收集和提交证据并相互攻击而得以实现。法律容许当事人及律师在开庭审理前会见证人,甚至并不禁止律师对证人的训练,[23] 这种训练不会影响证言的证据价值。两大法系对待当事人及律师事先与证人接触的不同态度,源于诉讼结构的不同。
中国的诉讼结构与证人出庭方式存在一种结构性错位。中国的民事诉讼结构属大陆法系,证人的询问和审查等皆采取大陆法的方式,通常由法官直接询问证人,当事人及律师询问证人须经法官许可,法官通过询问证人并结合其他证据对证言进行审查、核实和确定其证明力。但在提出证人或证人出庭方式上,实践中却主要采取普通法的做法,由当事人及律师寻找和提出证人,并通常在庭审时直接带到法庭,或申请法院传唤证人到庭。法官甚至事前并不知道当事人是否提出证人、证人是谁、要证明什么,[24] 因而在实践中存在证人主动要求作证的有趣现象,D和F法院皆有此例。[page]
这种畸形搭配不可避免会导致证人制度的机制失衡和功能紊乱。例如,它会对证人不出庭而无法证明的风险负担产生微妙影响。既然由当事人负责和保障证人出庭,《民事诉讼法》第66条及《证据规定》第47、55条又要求证人出庭,则证人不出庭而可能无法证明的风险就完全转移给了当事人。这又与中国法律对证人的定位产生了冲突:既然证人是“国家/法院的证人”,这种风险就不应(完全)由当事人承担,何况导致证人不出庭的原因[25] 主要来自制度缺陷、法治不健全、社会条件不具备和公民义务的普遍缺失。既然民事诉讼的目的是限制私力救济而实行公力救济,国家就应担负起确保证人出庭的职责。而正如上述,书面证言的证明价值实际上仍在一定限度内为法官所承认,故当事人事实上也未完全负担证人不出庭而无法证明的风险,未履行应负职责的国家以另一种形式(民事诉讼“潜规则”)对当事人作出了“补偿”。
与此相关,当证人证言是案件唯一的证明手段,证人不出庭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时,[26] 法官将如何对待证人不出庭呢?大部分法官(57.75%)会依证明责任分配裁决;法院对证人进行调查的22.46%;强制证人出庭的2.67%。这反映出证明责任分配的观念在法官中相当盛行。这也许可视为司法改革的成果之一,但它是否有助于改革目标的实现尚需深入考察,因为证明责任的分配实际上已部分地成为法官“卸责”的一个借口,只要当事人不能举证法官便依证明责任的分配判其败诉,而不愿花时间精力去发现真实,甚至不顾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这一点也与法院的案件负担相关,F法院案件负担重,体现在这一点上,就是依证明责任裁判的比例高达70.89%。我认为,如果证人证言是证明案情的关键证据,证人不出庭根本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法院应依当事人申请调查证人,不论是否属于《证据规定》第17条所指之情形,即适用于证人不愿出庭这种实践中的主要情形。
诉讼结构与证人出庭方式的结构性错位还直接影响证言的证据价值、证言在法官眼中的可置信度以及最终法官对证言的采信。当事人及律师寻找和提出证人,相互之间必然会发生一定的接触,从而往往会导致法官对证人可信性的猜疑。而证人在诉讼实践中事实上又没有依法条的逻辑成为“法院的证人”。特别自1980年代末审判方式改革推行以来,对抗制在中国逐渐受到重视,证据的收集、调查、提出被主流话语和法律规则视为当事人私人之事;而立法者显然没有想到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证人被蒙上“利害关系”的面纱,从而直接影响证言的可置信度和法官对待证言的态度。这种“双面挤压”导致转型司法中证人证言的作用低下。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如果证人是“国家/法院的证人”,则有必要限制当事人及代理人与证人的审前接触,若违反将导致法官眼中证人可置信度的下降;如果证人定位于“当事人的证人”,则法律须对伪证行为规定更严厉的制裁,并鼓励当事人的对抗,促进法官对伪证的识别,提高伪证行为被发现和处罚的概率,增加证言的可置信度。中国证人制度的重构,必须考虑证人的定位与诉讼结构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
既然无法限制当事人与证人的审前接触,或限制其接触将更难促使证人作证和出庭,则证人定位于“当事人的证人”便属不得已之选择。该建议似乎只是现状的合法化,对现实并无太大改变,但实际上会产生较大影响。比如,证人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既已公开化,法官便无法以此为由拒绝对证言作实质性考虑。尽管短期内这一制度安排未必会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法官对证人的信任度,但长远而言,“当事人的证人”所要求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包括证言收集、证人出庭、交叉询问、证言审查机制等)将促成中国诉讼体制从法院干预型向当事人主导型的变革,证人制度将更完善更科学,最终有助于增加证言的可置信度和法官对证人的信任。
七、结语
尽管本研究存在一些缺陷,如样本有限,问卷调查主观性较强,但就本文而言,上述材料和分析基本上可说明问题。调查和分析表明,在转型中国,证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因案件、地区、法院等不同而不同。一般说来:证人证言的数量与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书面程度成反比,采取书面形式越多,发生争议时出现证言的数量就越少;反之,证言出现的概率就越高。证人证言与书证、物证等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当事人提出成本更高、程序更复杂、采信率更低的证人证言的激励微弱。相对成本更低、可获得性更高的证据,更容易受到偏好。若有替代性证明方式,对证言的需求将大大降低,但在缺乏书证、物证的场合下证人证言的作用不可替代。
中国法律低估了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在转型时期的司法实践中,证人的作用进一步被轻视。[27] 即使案件可通过证人证言来证明,当事人、律师和法官也很少利用;即使证人提供证言,也很少出庭;即使证人出庭,法官也多不采信。证言的证据价值低于其他证据,这一点因诉讼结构、法律制度、司法传统、文化因素、法官素质、社会环境等复杂因素而成为现实。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涉及证人证言的收集、提出、证人出庭、询问、法官审查和判断证据等一系列环节的机制失调,既有制度本身的原因,也有司法运作不规范、大陆法书面重于口头的司法传统、法官水平不足等因素的影响,还存在社会背景尤其是信用环境方面的原因——信任丧失,谎言盛行。要使证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事实发现、纠纷解决和正义实现,须从多角度进行全方位的努力。
法官与证人之间信任的建立关键在于制度,应从诉讼结构的协调和转型入手,并以此为目标,构造一套更完善、更科学的证人制度。制度设计主要考虑两大目标:一要确保证人出庭作证;二要保障证人陈述真实,法官不排斥证人证言。证人应定位于“当事人的证人”;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证人作证则构成对国家的强制性义务,并以严格的法律责任为后盾。对前者,主要采取正面激励措施,由当事人提出证人和促使证人出庭,辅之以完善的强制证人出庭的规则(但对此不必期望过高)。证人之所以出庭,主要是因人情利益的激励。在补偿与收买证人之间也并非没有适当的平衡点:在避免收买证人嫌疑的前提下,可适当提高证人出庭的补偿标准,如在目前“平均薪酬”的基础上翻一倍,使证人出庭动机不因经济因素而受抑制。对后者,主要采取威慑对策,旨在通过事后制裁诱导证人说真话,同时通过完善对抗制而更充分发挥其本身的事实甄别功能,以及提高法官的事实判断力。有效的威慑机制之关键,既在于提高惩罚的严厉度,更在于严格执法,违法必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惩罚的积极性,若法官对伪证毫不介意,伪证必定盛行。法官追究伪证的激励因而至关重要,对此既要提高法官惩罚伪证的收益(如规定追究伪证行为相当于一定的工作量),降低惩罚成本,也需简化处罚程序(如法官可直接罚款,无需经院长批准),更应倡导法官树立司法权威不容挑战之观念。对证人,要通过制度及其执行,逐渐培养其一旦出庭便须陈述真实的意识。当然,这种“双管齐下”的激励机制多大程度上能被有效实施仍是一个问题,但这并非制度设计本身所能解决的,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法治环境。[page]
证人证言的收集和提出系当事人之事,法院只在有限的情况下补充,如依当事人申请调查证据。言词主义应明确规定为审理原则,除法定情形外证人须出庭;但书面证言的价值不应一概否定,相关规则还需进一步完善,包括规定书面证言的格式,格式文书上载明伪证的法律责任等。询问证人可移植普通法系的交叉询问制,即使目前在实践中可能存在“尴尬”,但它是保障当事人基本程序权和提高法官事实判断力的重要手段。法官对证言的采信,应透过证人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的迷雾,集中审查证言的客观性和关联性。有关证人的规则可借鉴普通法的证据规则。法律也应规定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就人的因素而言,法官对证人证言的态度过于消极,应当令法官清楚:证人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关涉到案件的正确处理和正义的实现;法官信任的重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
倘若司法过程中证人证言的作用继续这样失落,只作为一种流于形式的证据种类,证人证言少,证人不出庭,没有对证人犀利的交叉询问,法官对证人缺乏信任,则事实上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诉讼制度。重新发现证人的价值,促使证人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矫正有关证人提出和出庭等方面诉讼结构的错位,重建法官对证人的信任,继而实现诉讼结构从法院干预型向当事人主导型的变革,因此成为司法改革和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23]“律师可以探查证人的记忆,如果证人不擅文字,律师则可建议证人如何表达自己对事件的陈述。 . . . . . 一名善于操纵的律师,可以以谈话的形式为易受暗示影响或不讲道德的证人策划证言。”哈泽德、塔鲁伊:《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张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95. [24]2000年F法院受理一起工伤案件,第一次开庭原告带来了2位证人(其老乡),第二次开庭时被告则带来4位证人(该厂工人),法官让“每位证人只讲二分钟”。
[25]原因主要有:(1)立法方面:立法不明确、不科学,如规定单位作证不合理,未规定证人出庭方式、作证的程序规则、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拒绝作证特权等;证人的权利义务失衡。(2)执法方面:法官对证言态度消极,证言采信率低;证言的书面化趋向导致证人出庭的需求降低;法官对拒证行为听之任之;证人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出庭补偿费用(交通费、食宿费、误工损失等)不落实;对证人保护不够,对报复证人的行为打击不力。(3)证人方面:不愿卷入纠纷,怕得罪人、被报复;不愿浪费时间精力;法律意识淡薄,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认为作证效用不大。
[26]此类情形,如民间借贷案件唯一的证人,遗嘱继承案件中口头遗嘱的见证人,不愿作证;以监护人不尽监护职责为由请求变更子女监护权的案件中,只有被告的邻居知情,但不愿作证。50.27%的法官承认遇到过此类情形,其中D法院为82.86%。
[27]这种轻视证言、重视书证和物证的制度,理论上会激励人们进行民事活动时更多采取书面形式,尽可能保存物证,这样在争议发生时就可利用可信度更高的书证和物证。商事行为更多采取书面形式,与上述激励机制相关(尽管有研究表明,企业签约通常不是为预防纠纷,而是为自我约束,Stewart Macaulay, “ Non-Contractural Relationships in Business, A Preliminary Study.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8 No. 1, 1963, pp. 55-67. )。但这种激励机制有许多“死角”:不少情况下人们根本没有诉讼风险的预期(普通人涉讼概率低,1999年中国每10万人口民事案件数量仅403.23件);或不太可能事前预测纠纷的发生(若预期他人会赖账,就不会借钱);或无书面材料存在之可能(如人身侵权);或应对未来的纠纷可能产生较高成本(如婚前公证可能妨碍情感交流)。
声明:该作品系作者结合法律法规,政府官网及互联网相关知识整合,如若内容错误请通过【投诉】功能联系删除.
相关知识推荐
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欠钱不还的情况,但是很多这种情况都是会进行相关的和解最终不会走向上诉的道路,但是到无法调节的底部的时候还是会用上速来解决问题。那么,欠钱被
在离婚案件中,证人证言是常见的一种举证方式。但是,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很少有证人愿意出庭作证,而只愿意以书面的形式作证,那么,证人不出庭的证言是否有效力呢?实际上
医疗事故赔偿纠纷的诉讼时效为三年,应当自受害人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申
医疗事故中医院若不予赔偿的,当事人可以与医院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
医疗纠纷中的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调解协议书反悔了的,无法自行撤销,必须经人民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之后才可以重新达成新调解协议或者提起诉讼。我国《人民调解法》规
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包括有: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的;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的;限于
医院出伪证若是构成伪证罪的,会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